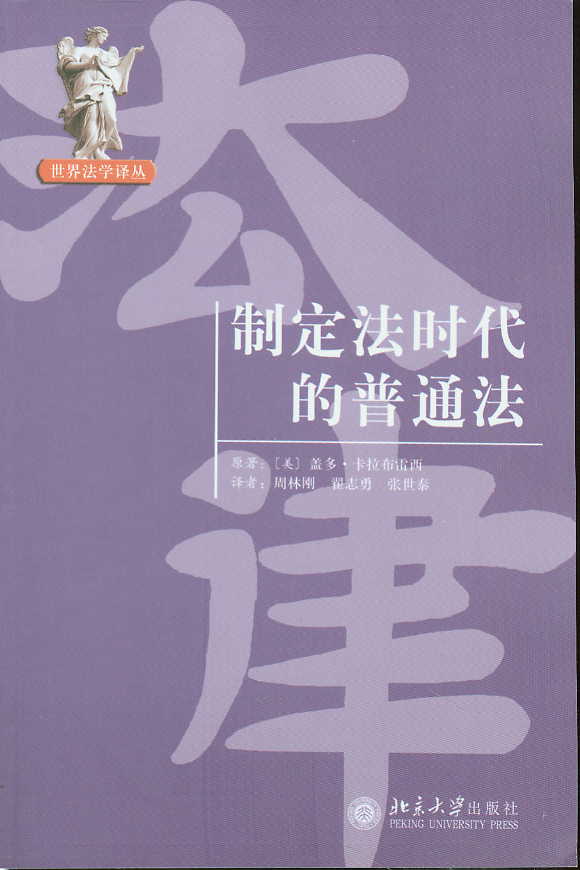
第十三章应变之道的危险
读者也许尚未确信,对我一直在分析的应变之道的公开宣示会是合适的。但假设我们对下面这几个方面达成了一致:(1)在我们的体制中,分配惯性负担的司法权力是有用的,并且可能是必需的;(2)部分出于这个原因,法院正是在从事着诸多我所建议的事情,不过是以间接的方式,而且是通过虚构和各种遁词来运作的;(3)为完成必须实现的任务,无须将法院推向对它们来说是困难的技术性事务;(4)被法院运用的间接的方式,对于将法院限制在它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益处;(5)立法机关对这一应变之道的明确但有限制的认可,可以成为它适用的先决条件。尽管如此,看起来最为公开和直接的从事某事的方式,并不总会是完成那一事情的最佳方式。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对这一司法权力的公开支持是否会带来这样的危险,它使得与对这一应变之道的坦率的认可相比,遁词和把戏(tricks)能够更好地实现这个普通法功能。
主要的一个危险,并不是使法院与立法机关负担过重,而是假如有这样一个教义,那么即使是在我们不想它得到适用的时候,它也是有可能被适用的。在他最近的一部主要著作中,亚历山大.比克尔不仅照常批评了布莱克法官对于绝对话语(absolutcs)的运用并得出结论说,它们并未能够限制住最高法院使其不致走过头,不过更为重要的在于,他同样列上了弗兰克福特法官控制司法自我扩张的限制性观念的败绩。在比克尔看来,坦诚的方法失败了,因为无论法官怎样反复地重申限制的必要,一旦一个特别有压力的案子摆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超越这些限制。当然,这是任何一种并不绝对的(noncatcgohcal)言辞都具有的危险,无论我们怎样努力通过警告来限定这些危险;假如我们承认在制定法之上的这样一个司法权力,那么这就是要承担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危险,无论怎样用学说的细密化来限制它。
比起比克尔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也算是“法律”的例子。我们都能经常发现,某个委员会被任命去决定是否应当从事一项研究以便解决一个难题(flu a jOb);但它立即就成了解决这个难题的研究委员会。正是存在空缺的可能性得到承认这个事实,对于制造空缺大有帮助。而在制定法之上的司法权力得到承认这个事实,也能很好地为它的运用进行辩护。这个趋势在对抗制的体制之下被加剧了。去认可一种教义或者一种可能性,就是鼓励律师们力争去适用它。假如他们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的话,律师们通常都会在即使并不应当适用的情况下,力争适用的可能性。情况好一点的,这将成为对时间和精力的巨大浪费。但是它常常不止如此。适用的主张被提出来这个事实,能使新闻媒体和大众以为这个主张获得了胜利;这反过来使该主张在以后更有胜出的可能(我们都已经看到那个简单明了的变换,由此,一个提出巨额赔偿请求的稀奇古怪的侵权案件[原告]败诉了,但是案件被报道得暧昧不明,以致该案件被人们普遍地认为一一包括将要成为陪审员的人们一一是一个支持那个古怪的请求[outland-ish rcsult]的判决)。危害并不就在此打住了一一可以主张一个教义的事实给这一教义制造出一种可敬的气象,至少在棘手的案件里,这给法院施加了一种压力,驱使它们接受那个主张。
毫无疑问,对应变之道的公开认可,有时会使它在不应当对制定法进行司法审查的一些情况下得到运用,而假如法院被剥夺听取律师基于各自立场而作的主张的可能、从而不得不依赖它们自己的想象去寻找实现它的方法的话,又会[在该适用的时候]得不到适用。在法律上,承认一个教义就是使它具有分量,赋予它凝聚力,允许它在法制图景的未知部分发挥影响。
这一过度运用的危险性很小,因为司法滥用(不像对于宪法裁判权力的司法滥用)总是可以通过立法机关的行为来补救一一这个说法还不是一个充分的答案。相对于承认普通法的监督这个原理,实际可行的替代选项只能是诉诸宪法,在这个意义上,上述说法是足够可靠的。并且,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将构成承认这个应变之道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司法滥用并不能仅仅由于立法机关拥有最后的权威而得到充分的补救。容忍此类司法滥用,意味着接受这个可疑的主张:与法院自己任意的偏好比起来,过去立法机关的一个起点对于正当性的主张并不更强有力一些。或者它意味着否认在我们的体制中立法迟钝是一个重大的事情,因此也就否认对于起点的分配会对结果、对法律将会如何,产生重要的影响。 另外,还有其他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立法机关推翻对该原理“任意”的司法滥用的能力,并不足以消除我们的担心。首先,假如立法者容易变得习惯于去推翻法院[的判决],这将趋向于妨碍重要的司法职能的发挥,这些司法职能依赖于法院判决的终局性。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形,在其中,立法机关已经变得如此习惯于推翻法院[的判决],以至于诉讼当事人自然而然会试图去使一般诉讼当中的结论在立法的层次被推翻。其中有一些确实不可避免地会实现,并且甚至是适宜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体制并不是这样一个体制,其中有一个受理从最高的司法法院的裁判而来的一般性上诉的、最高立法法庭(1egislative court)。
其次的一个危险则是,为了避免前一个危险,立法机关会不乐意去推翻法院[的判决],甚至当法院判决一条制定法的规则需要修改的裁判并不正确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样一种围绕司法的普通法判决的氛围的产生(与存在于宪法裁判周围的氛围相似 ,会加强惯性的力量,甚至比今日更甚,并且可能使司法的普通法判决变得更有力量而超过它合适的程度。
最后,可以想见,由于意识到这两个危险,法院自己将会变得不乐意去运用应变之道,甚至在适用它是恰当的时候也是如此。一种“除非确实需要,不然省着不用”的哲学可能就会产生,这将使我们退回我们的起点处一一被陈腐过时的制定法卡得喘不过气来。
我并不是说,这样一个过程终将达成的平衡,会比我们现在正在走向的结果更坏。毕竟,普通法规则之上的司法权力存在着,而且它的运作也带来许多我所列出的那些危险。当它结合了源自解释、消极德性以及直接的宪法判决的、在制定法之上的司法监督的时候,极有可能的是,我们已经对存在于过多的司法干预(judicialdetermination of results)和立法太过频繁地推翻法院判决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以为然了。我的要点并不是要在各种次优(second.bests)方案中选择一个,而是要求强烈地认识到,对我们一直在考察的这个应变之道的存在的承认与接纳,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并且也不能因为立法机关确实保有最后决定的能力而把它当作是无关紧要者弃之不顾。
然而最终,我们还是不得不卷人次优选择这样一种分析当中去。我们将要考虑,由于承认这样一个原理而带来的危险,是否就比继续无视这个原理的危险更小。我们将要推测,假如承认带来的危险会变得严重起来,变得比不承认它而带来的危险更为严重,那么这些危险是否多多少少是可以得到补救的。我们已经考察过不承认所带来的危险,它们为每一种正为法院所运用的、使法院具有制定法上之权力的教义所固有。然而,我们尚未留意这些一一在运用遁词以及滥用遁词中的一一危险的总量,并把它们与由于承认应变之道而带来的危险的总量作个比较。
不过,在这样的比较之前,我们必须问问我们自己,利用所有那些为达成司法对过时制定法在某种程度上的控制而已经被运用的教义,并且仅仅当每一种教义在其自身的教条性限定的范围之内是恰当的时候才运用它们一一这是否能够提供一种有力的武器去对付制定法的老化问题。换言之,我们必须要问,对惯性负担作分配的工作,是否能够通过运用所有已经为法院所运用的教义而无需创造一个新教义,以坦率的方式来完成。
答案在本质上是经验性的,通过观察当前的司法行为可以找到这个答案。考虑一下法院是否只是在恰切的限制之内才行使下述权力的:它们审查普通法规则的传统权利;它们诚实地一一在模棱两可的案件当中则是功能性地一一解释制定法的权力;它们将授权不明或宽泛的制定法,或者将侵犯宪法影射区的不和谐的法律退回重新审议的权力;以及它们宣布违宪的制定法无效的义务。每一个答案都必定是“否”。我们已经看到[法院]竞相采用平等保护这个原则来废弃那些明显是合乎宪法而有效的法律;解释的运用,甚至把最大的诡辩家们也视为是在运用解释;消极德性被发展成为一种服务于“种类繁多的随心所欲的干涉主义”的工具。换言之,我们已经看到,手头的工具对于法院感到紧迫的工作来说,还远远不够充分。让我们加上:明显过时的法律继续存在,它们一一假如它们是普通法规则的话一一可能会被修改并且可能被当前的立法机关所颁布一一但又相当难以意料;类似落日规则这样的观念的流行,这些对于对付法律的老化这个难题来说,都明显是不够的。结论必定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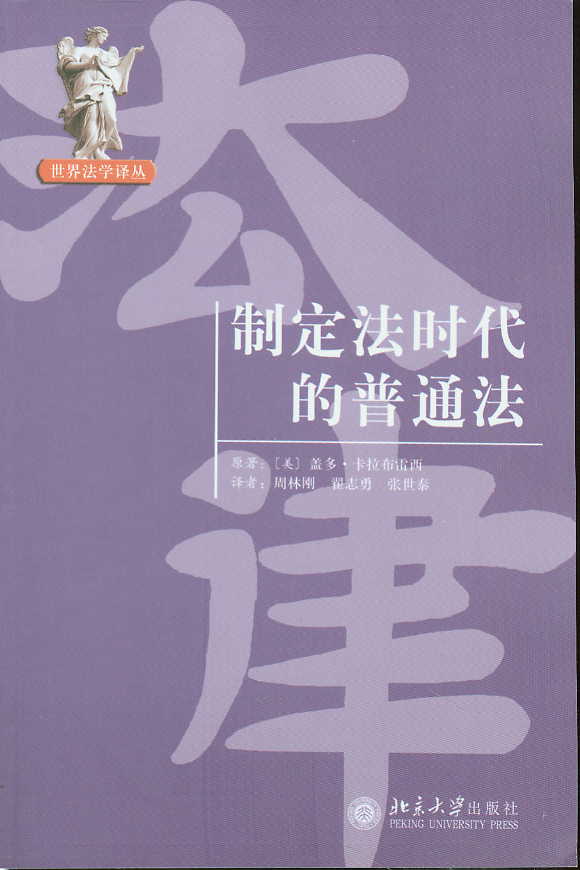 第十三章应变之道的危险
第十三章应变之道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