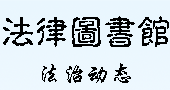当前位置:法律图书馆>>法治动态>>出版动态>>英国强制执行法
英国强制执行法
http://www.law-lib.com 2014-3-18 9:50:54 来源: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1月
价格:65元
本书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英国强制执行的理论与实践。作者结合二十五年来上海法院的司法实践,以及他在英国利物浦郡法院作为访问法官“陪审”时的体验,对英国强制执行权的定义,执行员“市场化”和“司法行政化”双轨制的运行模式,自力救济性质的欠租扣押和没收租权,金钱给付判决与逾期税、费在执行中的冲突及协调,强制执行与破产的衔接,不动产交付判决执行中强迁的特点,征地强迁与拆违强迁的异同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并在比较的基础上,就民事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强制执行与破产的关系,以及执行的冲突与协调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全书48.8万字。
张永红,男,1966年8月生。三级高级法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监督处副处长,国家法官学院上海分院兼职教师。2007-2008年度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学者(Chevening Scholar),英国利物浦大学法学硕士。复旦大学法律硕士。南京农业大学农学学士。曾在上海金山法院工作 20年(其中14年多在基层法庭工作),办过不少民事、商事和执行案件,担任过立案庭庭长、执行庭庭长、研究室主任。曾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处处长。主要研究兴趣:强制执行法,个人专著有《英国强制执行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负责编撰(副主编)的著作有《强制执行》(法律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法律书评]杰拉德•费兹捷勒(Gerard Fitzgerald):《英国强制执行法》序
我与永红相识于五六年前。当时,他在利物浦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我在利物浦民事家庭法院担任地区法官。永红知道他在英格兰的时间有限,决定利用那次机会尽可能多地探悉英国的法律制度和英国和欧洲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坐在我和其他法官旁边听、看法院案件的审理,还包括很多其它事情。
永红不仅对英国法院适用的法律原则感兴趣,还对法律实践充满兴趣。这包括法院案件的准备;律师和其他职业人员的作用;法官与法院行政管理人员的关系;起诉和抗辩的费用(通常非常高);法院判决的执行方法。我觉察到英国的有些方法对永红来说很惊异,但有些问题与他在上海当法官碰到的事情很相似。
一直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永红能够非常快的消化、理解和评论非常复杂的技术性法律问题。这可都是些用英文讲授的问题。他的成就不仅反映了他的能力,也反映了他在英格兰期间所作的巨大努力。因为永红的书是用中文写的,所以我未能给他提供有用的帮助,但是,无任怎么样,我很快就认识到,对于英国强制执行法,永红知道的要比我多。
能够认识永红并成为他的朋友,我很高兴。能够在令人惊叹的上海再次与永红相见,我非常开心。尽管相距甚远,但我真诚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联系。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不同国家的人们相互学习和理解是多么得重要。我确信永红的书一定能够增进这样的理解。(本文作者系英国地区法官,张永红译)
[法律书评]刘建:强制执行理论与实践的前瞻性思考
对于外国的法律制度,伏久者已不满足于简单的翻译介绍,而是立足我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分析,由此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逻辑体系,令人欣喜。复旦大学出版社近日推出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张永红先生的著作《英国强制执行法》就是典型一例。
说起强制执行,国人并不陌生,但若提到英国的强制执行,国内确实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本书作者是一位有着20年基层法院工作经验的资深法官,办过不少民事、商事、执行案件,对我国的强制执行有着很深的感悟。同时,他又是2007至2008年度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学者,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在利物浦郡法院作为“访问法官”、“陪审”过近一年。所以,他对英国强制执行法的探析,既注重法律本身的考证,又注意法律的实施效果,既考察强制执行法的历史发展和内在规律,又分析现行法院判决、欠税和欠租、欠费执行中的冲突与协调,既探析征地强迁制度的共性,又分析拆除违法建筑程序中强迁的法律特点,字里行间充满着求真务实的精神。这些问题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碰到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他在论述过程中结合我国强制执行理论和实践所作的比较、分析,针对性强,具有很好的启示、借鉴意义。
全书48.8万字,凝结着作者整整六年的心血,弥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特别是结语部分就民事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强制执行与破产的关系,以及执行的冲突与协调这三个问题提出的观点,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读了之后,令人深思。当读到英国房产税的强制执行时,犹如一场及时雨,酣畅淋漓,发人深省。
执行乃法律之终局和果实。“执行难”问题几乎是所有国家都经历过并依然面临着的问题,只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这一问题的表现有所不同而已。近些年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强制执行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受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执行难”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民法院执行不力的信访投诉还比较多;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现象时有发生;大量无财产案件堆积在执行程序中无法退出;执行人员的廉政风险还比较大;法院与税务等机构的执行冲突还需协调;民间“讨债公司”的追债行为禁而不绝;征地强迁、违法建筑拆除、违法停车整治等工作中的矛盾还比较突出……,作为一名长期跑在政法口的记者,我与作者一样,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努力,但离社会对执行工作的期盼总还存有不少落差?到底什么是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法的未来将走向何方?相信本书能为我国强制执行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能为我国强制执行的立法提供一些新的参考,能为我国法院、税务、征地和拆除违法建筑等机构的强制执行工作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来源:《法制日报》)
[法律人生]张永红:我的一位英国法官朋友——《英国强制执行法》后记
本书自2007年7月赴英留学时动笔,至今已整整写了六年。在付梓出版之际,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一位英国法官朋友——英国地区法官Gerard Fitzgerald。
一、认识Gerard法官纯属偶然
大学毕业20年后,我申请到了2007年度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那时我还在上海金山法院担任执行庭庭长。作为留学生,利物浦大学为我指派了个人辅导老师(Personal Tutor),关心帮助我的学习生活。他是英国利物浦大学医疗法及医疗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John Harrington教授,与我年龄差不多。那天他约我去他办公室,聊了聊我的学习生活情况,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助。我说学习、生活上的困难我可以克服,但不知你是否认识当地的法官,因为我想去看看他们的工作,想请你引荐一下。
说实话,当时说这句话时,也没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法学院的学生凭学生证可以去当地法院旁听庭审,但如果想约见法官,与他们交流,这就非常难了。记得当时他对我说,他可以试试。但过了一个多月,他没给我回音,我想肯定有难度,所以,这件事渐渐也就淡忘了。没想到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发email给我,说他还在努力为我联系,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回音,是因为他是通过他的一个朋友在帮我联系的,而这位朋友最近去非洲了,并问我是否还有兴趣去法院。我马上发email给他,说如果能联系到的话,最好,实在有难度,也不要太为难。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了email,说现在终于有一位法官愿意与我交流,但交流是双向的,所以约我去他办公室,想先听听我准备交流什么。我想他对我有点不放心,这也很正常,虽然他知道我是中国上海的法官,但毕竟只见过一次面,对我还不是很了解。
我按约到了他的办公室,告诉他说,我在中国上海的基层法院工作20年,办过很多案子,对法院的工作有着很深的体会,也碰到过很多困难,比如“信访”问题,“执行难”问题,所以我想去看看英国基层法官的工作情况,想知道英国法官在工作中有无类似的问题。他听了之后非常惊讶,说他对中国的司法体制及法院运作一点也不了解,相信利物浦的法官也会对此感兴趣。为此,他给我正式作了安排,并亲自陪我去利物浦郡法院。
那天约好9点30分在法院大门口碰头。但到了那里,John突然接到电话,是与他约好的那位法官打来的,说是碰到特殊情况所以没时间见我们,但已安排了另一位名叫Gerard Fitzgerald的地区法官接待我们。所以,结识Gerard完全出于偶然。工作人员将我们带到了一个会议室,Gerard向我一一介绍了其他10名地区法官。与我一一握手、问好、敬茶、表示欢迎之后,坐下来交谈。我暗暗吃惊,怎么这么隆重?
事后才知道,Gerard资格比较老,按他们的话说,是一位“父亲”级的法官(Father Figure),在法官中很有威望,平时大家都亲切地叫他Ged。作为一家基层郡法院,没有接触过中国法官,所以他们对我充满好奇。在他们看来,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国基层法官,怎么会有时间出来学习英国人自己都觉得比较难学的法律,而且还是英国外交部出的钱。因为在英国,拿到法学学士学位后如果想搞专业的话一般有两条路,一条是再读两年的律师职业课程,通过考试,到律师事务所实习后,当律师。另一条是通过硕士、博士搞学术。法官基本上都是从优秀律师中产生的,所以年龄都比较大,四十出头的年纪,才刚有资格担任法官,所以当了法官后不太可能再去读硕士。我向他们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告诉他们中国的法官很重视学习,这次到英国学习是在职学习。他们说,他们也有在职培训,但每年只有2、3天时间。上午10点,我随Ged去看他开庭。
二、第一次“陪审”
说真的,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很难想象英国基层法官是这样审案的。法庭的审判区像法官的办公区。一张大的桌子,上面放着很多书,还有录音机,电话机,并放着一大瓶饮用水。Ged安排我坐在他的旁边看他开庭,我就像“陪”审员,但只陪不审。“值庭人员”(Usher)为我倒了一杯水。那天上午,他有三个庭,每次庭审开始前,Ged总是向到庭的律师及当事人介绍说,这是来自中国上海的张法官,他是“志奋领”学者,在利物浦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他今天要观看我们开庭,并询问当事人有无意见。见习近一年,我没碰到有提出异议的。从当事人及律师的神色看,他们觉得也很新奇。后来时间长了,经常来的律师也有点面熟了,有一次正巧在街上,还碰到过一位律师向我打招呼。
Ged开庭就像医生看病。当事人就像“病人”,通知的庭审时间一般都是上午10点,或下午2点。当事人到庭后先向“值庭人员”报到,然后就等在庭外由“值庭人员”按照“先来先安排”的原则引进法庭。如当事人未到庭,案件就注销(dismiss)。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当事人已和解。如确因正当理由未能到庭,当事人可申请恢复审理。地区法官开庭不穿法袍(但我去英国高等法院及上诉法院旁听案件时,看到法官都穿着法袍),除疑难案件外,一般都不用书记员。庭审时事务性工作由“值庭人员”负责。庭审是录音的,没有书面记录。法官坐在审判区。以前法官没有私人的办公室,审判区还兼作法官的办公室(所以chamber一词兼有法庭和办公室的含义)。法庭没有固定的原、被告席,当事人及律师进来随便坐,座位都是面向法官的。见当事人进来,法官总是Good morning 或Good afternoon打招呼,基本上没有“全体起立”这样的程序(但也有个别法官比较讲究,喜欢这样做),倒是“值庭人员”进出法庭在门口时总要向法官鞠躬,这也是基于传统。当事人的律师一般在开庭前都已为法官起草好判决书、裁定书,经审理,由法官当庭在稿件上签名确认或补充修改;法官在庭审中作出的判决、裁定都是由原、被告的代理律师即时作好书面记录交法官签名后,由律师送交法院管理机构的立案部门打印的。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由法官当庭书写后交当事人送交立案部门打印。所以法官很会“借力”。经历的最短一次开庭只用了1分钟,是开庭宣判,笔者随法官进入法庭,书记员喊“全体起立”(这也是笔者碰到的唯一一次“全体起立”程序),就坐后,法官请大家坐下,问判决书收到了吗?双方当事人和律师都说收到后,法官即说那就不念了,并问双方还有其它事吗?双方都说没有,之后法官就宣布开庭结束。看到笔者很惊讶,法官解释说,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很长,他已在宣判前寄给了双方当事人,免得宣判时再念,浪费时间。
三、交流时,我拿出了录音笔
记得第一天的中饭是在法院吃的,还是在那间会议室,吃的是汉堡。边吃边谈,Ged向我介绍了他的工作情况。我拿出录音笔,问他是否同意我录音。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回去之后再听听,一则可以提高英语,二则可以加深印象。他表示同意。下午是4点离开法院时,Ged给了我他的家里电话及手机号码,并对我说,如有什么事情,可随时与他联系。原以为去一次就结束了,但因为我在听录音时有几个问题搞不懂,便打电话问他,他说电话里讲不清楚,约我下个星期去法院再讲。没想到从此每周一天去法院成了我的必修课。第二个星期是星期三去的,我指着听写下来的内容问他,他大吃一惊,说我怎么这么认真!我说我真的很想了解英国法官的工作情况,于是他便非常认真地为我讲解了我提出的问题,像第一次一样,我拿出了录音笔,录下了我们的交谈。此后我每次去法院,都带着录音笔,录下了一个中国基层法官与英国基层法官、法院工作人员、执行人员的友好交往。
交谈中我才知道,那间会议室是法官专用的休息室。上午开庭前9点45到10点,法官们总会聚在休息室喝“早茶”,聊聊案件,对较难处理的案件,听听其他法官的意见,这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法院管理机构给法官提供的服务很周到,茶水、茶点一应俱全。法官“早茶”时,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询问法官中饭想吃什么,并作好记录,做好准备。问我喝咖啡还是茶,我说茶,不要加牛奶,茶包留在茶里。事实上,我还是保持着在国内的喝茶习惯。此后,每次给我泡茶,他们都不加牛奶并把茶包留在茶里。我每次去法院,也总是在9点45分到,与他们一起“早茶”后,即随他们去开庭。他们把我当作访问法官(visiting judge)对待,而不是法学院学生,对我国的法院、法官及司法管理充满着兴趣,其中一个50多岁的法官还在学中文。法院的工作人员见了我,就像见到英国法官一样,尊称我Sir。
Ged告诉我,他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当了二十年律师,经自己申请、有关法官的推荐、国家法官任命委员会考核,先成为“代理地区法官”(Deputy District Judge),或称兼职法官或预备法官,一年在法院办案一、二个月,其余时间仍是律师。在法院办案期间国家按劳付费,所以又称“付费法官”(Fee-paid judge)。三年后被任命为全职地区法官,由国家发工资,故又称“工资法官”(Salaried judge)。已担任法官十余年。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主要的原因一是法官社会地位高,受人尊重,收入有保障。地区法官年薪十万英磅,去税后实到手6.5万(法院经理才三万多一点,与法学院的教授差不多,法院执行人员一万六、七千,一般工作人员一万多一点);二是用不着怕上诉改判,也用不着怕投诉。有时候直觉告诉他有些案件当事人事后会投诉,但有关部门从未找过他。所以法官基本上可以在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保持着司法的独立。如遇重大案件自己觉得有压力,可以提交上级法官审理,上级法官也可找再上一级的法官审理,上级法官不会推诿。三是要比律师自由,虽然工作日法院管理机构始终让他“保持忙碌”状态,但八小时外的时间是自己的,用不着像律师那样随时有可能被客户叫去。同时每年还有较长的假期。他一般9点到法院,先看一些材料,10点开庭,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庭开到4点结束。
四、我全家去Ged家做客
第三次“陪”审结束后我告诉他,下周我就不来了,因为我妻、女来英看我,我要陪她们出去转转。Ged非常好客,邀请我及妻、女去他家做客。他家住在Chester,离利物浦40分钟的车程。那天他专程从Chester开车到利物浦接我们到他家。问我女儿想去哪里玩,我女儿说去动物园。我为我女儿感到自豪,小学四年级,也能讲几句英语,而且一点也不怕生。我妻有点拘束,因为她不会讲英文。他们夫妇陪我们一起去动物园。我要把门票钱给他,他坚持不要。累了坐下休息,买来冰淇淋。陪我们参观Chester古镇,到其原来工作过的律师事务所参观。其妻先回去做饭,等我们回到他家时,饭已做好,招待我们吃饭。Ged说今天其妻做了最拿手的菜,一般是在圣诞节吃的。其妻问我平时在家里做不做饭,我说在家里基本上都是我做饭,其妻要Ged向我学习,因为Ged不会做饭。吃饭时Ged告诉我,他们的很多法官都出身富门,但他是爱尔兰人,工人阶级出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当上了法官。他的妻子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得知我妻是中医,Ged便说他的手经常抖动,看过很多医生都没什么效果,问中医是否有效。这下可难住我了,因为我妻说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东西,我是无法翻成英文让他听明白的,所以只是简单地建议他试试针灸。他家现在住的200多平米的别墅,是他十年前用20万英磅买下来的,按现在的房价已升值到50万英磅,他为此感到很高兴。三个儿子都大学毕业已工作,女儿在北京的一所小学当过一年的外教。他与妻子去过北京看女儿。他们非常赞叹中国的发展,说没去过中国的人是很难想象的。在北京看女儿时,他们喜欢乘地铁体验中国人的生活,喜欢去小饭店吃中国菜,还吃过火锅。孩子小的时候没时间,现在孩子都工作了,业余时间就与妻子出去旅游。我带去了一幅金山农民画,他们非常喜欢。临别前,他们送给我女儿一个小玩具,Ged又开车送我们回利物浦。
五、回国前的礼别
我回国前,一直在考虑告别时送什么礼物意思意思。想感谢他们的热情接待,特别是我的8篇每篇5000字的课程论文和一篇15000字的硕士论文都是Ged帮我润色修改的。他非常认真,帮我把标点符号都改了出来,对我提高英文写作水平帮助很大,也使我拿到了较好的成绩。一个劲地夸我写得好,说很难想象一个中文是母语的人能用英文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在一年的交往中,也使我学到了活生生的工作语言。我对他说,想送点小礼物给他们,问他合适不合适,并问他一共有几位法官。他问我为什么要问“一共有几位法官”,我说,我在准备礼物。他便对我说,你没有必要每个法官都要送,并建议说,上次去他家时送给他的画很好,告别时可以送一幅给利物浦的全体法官,这样他们可以把画放在会议室,每天看到画,就会想起你。我很感谢他的坦诚,于是便请回国的同学在回校时帮我带了过来,并为Ged准备了一份有一百个“福”字的竹简。在“早茶”时我向他们告别,在院的十位法官签名送了我一幅画。我送了他们一幅金山农民画,他们很喜欢。然后我到Ged办公室,拿出了百福竹简,说“福”字在中文里是一个最好的字,倒着挂表示“福到”,他非常感谢,说他会把它和上次我送给他的金山农民画放在一起。
在我回国的前一个晚上,Ged夫妇专程从Chester开车到利物浦为我送行。饭店由我定,请我吃饭,他的妻子给我妻买了一条裙子,给我女儿买了一件T恤衫,作为礼物要我带了回来。我选了一家中国餐馆,要了一瓶白葡萄酒,因他要开车,只是象征性的喝了一点。所以一瓶酒基本上都是由我与他妻对分的。讲起法官酒后驾车问题,他说他的有些同事平时也喜欢喝酒,但他们会相互监督提醒。说起法官与律师的关系,每年他总会很高兴地接受他曾工作过的律师事务所的邀请,参加一年一度的律师聚餐年会,但相关费用由他个人承担,该所律师代理的案件,他会主动回避。除了年会外,法官不会与律师一起吃饭。法官都很自律,即使是朋友间的聚会,基本上也都是AA制。在法院吃中饭,法官与法院工作人员的用餐场所也是分开的。饭后,我说我来买单,他不肯,说如果在上海的话,由我招待,他们没意见。但服务员小姐还是习惯性地把账单拿给了我,当她看到是Ged付钱时,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因为那个时候正值学期结束,中国留学生回国前请导师吃饭告别比较多见,外国人请中国人吃饭的情况比较少见。一共50磅,Ged带的现金正好是50磅,考虑到还要付小费,便拿出信用卡,当我对他说在那家中国餐馆用餐,如现金支付可打九折,也用不着付小费时,他感到很惊异。我悄悄对他说,今天的服务员肯定没想到坐在这里的是两个法官。Ged说是的,他们一般很少出入公共场所,无论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法官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及社交圈,非常注意维护自己的名誉。用他们话讲,名誉是法官的生命,所以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生活细节和业外生活。握手告别,在我不经意之间,他的妻子在我脸上给了我一个吻,我茫然不知所措,Ged对我说,这是爱尔兰人传统的告别方式,并说他会很自豪地对他的朋友说,他有个在中国上海当法官的朋友,我说,“你是我在英国最好的朋友”。
我真的要感谢这位朋友,在他的帮助下,使我能有机会结识了其他法官,结识了法院的工作人员,并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对英国基层法院的实际运作有了全面直观的了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要比一张法学硕士学位宝贵得多。在《英国强制执行法》的写作过程中,我曾理出100多个问题,通过skype打了不少电话向他请教,他总是那样友好,那样耐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付梓出版之际,笔者还要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上海金山法院郭俭、张斌两任院长,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不太可能40多岁出去留学。感谢英国外交部“志奋领”奖学金项目的资助。感谢利物浦郡法院法院经理Jean Martin-Hall、执行员经理John Armiit。感谢利物浦大学医疗法及医疗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John Harrington教授和法学院院长Fiona Beveridge教授。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感谢我的妻子原谅我双休日三缺一时仍拒不陪她打扑克;感谢我的女儿每天晚上盯她做作业时她总是顶嘴说“你管你自己写书吧”,使我有时间集中精力专心写作,完成本书。(作者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
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书推荐语
“执行难”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执行难”几乎也是所有国家都经历过并依然面临着的问题,只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这一问题的表现有所不同。我国现行的强制执行制度借鉴了不少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对英国强制执行法关注不多。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英国强制执行理论与实践的学术专著。书中对“押记令”及不动产押记后的“出售之诉”、动产的“书面扣押”、“中间人之诉”、“拘押”等制度的探讨,对健全和完善我国强制执行制度,化解“一套住房”执行难题、减少动产查封扣押对抗性、简化执行救济程序、提高执行威慑力等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尤其是结语部分就民事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强制执行与破产的关系、执行的冲突和协调提出的三个问题,为我国强制执行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我国强制执行的立法提供了新的参考,为我国法院、税务、征地和拆除违法建筑等机构的强制执行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考。
日期:2014-3-18 9:50:54 | 关闭 |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