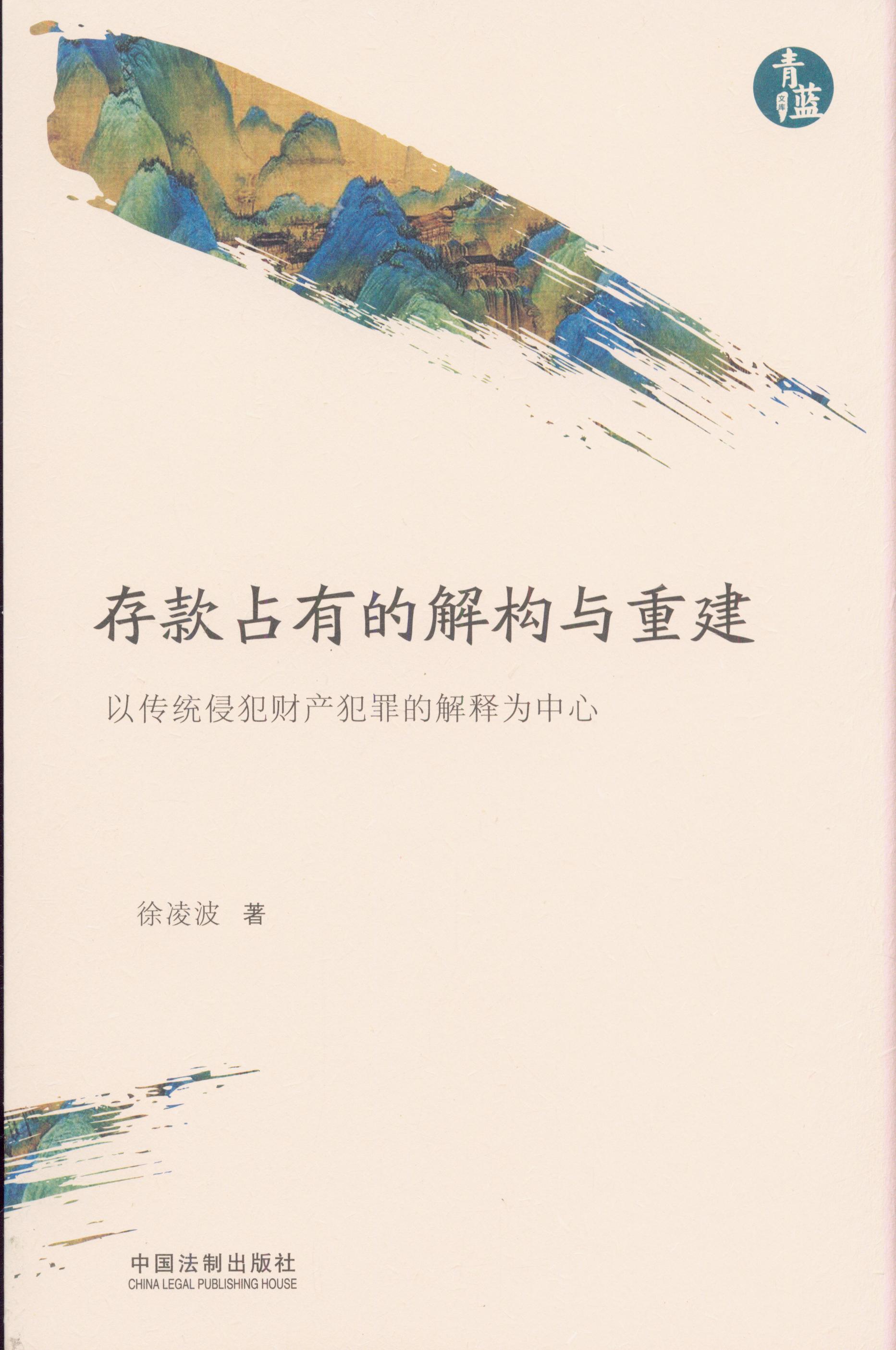
首先,存款债权的特殊性体现于我国刑法的明文规定之中。《刑法》第9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从条文表述看,刑法将公民储蓄视为公民“所有”的财产,与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其他生活资料置于同等的地位予以规定。尽管在这里使用了“所有”一词,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刑法认可了公民私人对存款的“所有权”,而应当理解为我国刑法上对于公民的存款债权给予了特殊的保护。笔者以为,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而非构建财产权利归属的等级和秩序,因此,就财产权利的区分与体系构建应当尊重民法上的规定,这不仅是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考虑,也是基于效率的考虑,在民法之外重新在刑法上构建新的财产权利体系,不仅浪费理论和思想资源,同时也容易导致讨论上的混乱而必须不断地重新对相关的权利进行重新定义。
由《刑法》第92条的规定衍生出来的问题在于我国刑法规定侵犯财产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的问题。我国刑法传统通说认为刑法所确立的财产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所有权,称为所有权说,张明楷教授曾经对此进行了批判,认为按照所有权说使得他物权以及债权都无法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内,显然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他指出,“根据所有权说,他物权不是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这显然过于缩小了刑法保护的范围,不利于发挥刑法保护法益的作用”,此外“民法上的所有权是与债权并列的,如果认为刑法只保护所有权,就意味着刑法不保护债权,这当然不符合刑事司法精神与司法实践”,因此所有权说、本权说、法律的财产说,“都是财产关系极为简单时代的产物,计划经济体制下,财产关系极为简单,所以所有权说得以流行。然而,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化,德日以及英美学说和判例的变化均表明财产关系的复杂化是占有说、中间说、经济财产说得以存在乃至成为通说的原因”。进而他提出,财产犯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但是传统的所有权说实际上是根据《刑法》第91条、第92条所确定的公共财产、公民合法所有的私人财产的范围来确定自己的保护范围的,从该条文表述看,所谓的公民“所有的”财产要广于当前民法上所理解的“所有权”,这是刑法上的“所有”与民法上的“所有权”之间的断裂和脱节。张明楷教授实际上立足于民法所确定的所有权概念来指责刑法所保护的公民“所有”财产过于狭窄,因而存在一定的误解。当然这种误解实际上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初期,民法上关于存款的所有权存在银行所有与存款人所有上的争议,其中前一种观点占据优势地位,认为“存款是存款人在保留所有权的条件下,把使用权暂时转让给银行的资金和货币。储蓄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信用行为,通过契约的方式,个人把或货币存入银行后,货币的使用权暂时让渡给银行,存款人仍然享有所有权”。这一观点与当时的法律规定相一致,《民法通则》第75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个人财产,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文物、图书资料、林木、牲畜和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以及其他合法财产。”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储蓄存款是指个人所有的存入中国境内储蓄机构的人民币或外币存款。”第3条强调:“国家宪法保护个人合法储时而言,刑法对于公民合法所有的财产的规定与民法对于存款所有权的规定是一致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存款所有权归属于存款人的观点日益妨碍了市场经济交易的发展,因而学说和立法上转而均接受了货币的占有即所有规则以及存款所有权归属于银行的观念,2007年的物权法便不再把存款列为公民所有权的对象,因此《物权法》在第64条规定了私人所有权的对象范围,即“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其中公民储蓄并未如<刑法》第92条那样列入在内,而是另外在第65条规定“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这是民法上对于存款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上的转变。
但与之相对刑法并没有因此而修改,而是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的观念。这一刑法与民法上的差异导致了刑法在存款问题上说理的混淆,固执于公民对存款的所有权这一观念上,使得理论和实践中的讨论需要不断地回到存放在银行内的现金实物本身。理论上,或是引进德日理论将占有解释为“事实上的控制支配”,而认为取款行为对现金的占有转移,因而将评价重点放在取款行为上,或是继受了后来发展出来的法律上控制支配理谂而肯定存款名义人的占有,或是进而误解法律上控制支配理论而认为非存款人的名义人也拥有法律上的控制支配。但是理论却忽视了一个问题,盗窃存款债权凭证,在现今的语境下不再是侵犯存款所有权的行为,而是侵害存款债权的行为,存款债权只是对应一定的金额的银行资金,而非对应作为被特定化的货币。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很好地坚持了德日的刑法理论以及民法关于所有权的概念,但却使得银行成为这类案件的受害人,而忽视了存款人存款债权的受损。民法对于存款的所有权归属的变化并未影响刑法对此进行保护,只不过由刑法保护公民个人的“存款所有权”变为了刑法保护公民的存款债权。考虑到刑法条文特别强调了对公民储蓄即存款债权的保护,将存款债权本身纳入“公私财物”的范畴内并不存在解释上的障碍。
从民法上看,存款债权是由银行信用所担保的,较之商业信用而言,存款债权具有最大程度的清偿可能性,也就是说存款债权的信用程度是最高的,法律制度对于此种债权赋予更多的优先性考虑,在银行破产的情况下,存款债权要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而获得清偿。从经济学角度看,银行的活期存款被纳入广义货币的计算当中。各种财产权利凭证、金融产品的产生,都促进了存款债权的流通,其流通性要大大超过普通债权。就刑法而言,刑法第92条中,将公民的存款从其他一般债权中分离出来,表明刑法上对其保护的重视。
摘自:《存款占有的解构与重建——以传统侵犯财产犯罪的解释为中心》P304-307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内容简介:在我国刑法的实务处理和理论讨论中,存款的占有至少具有四个层面的含义,即现金的事实占有、现金的法律占有、存款债权的占有以及基于存款债权的占有而产生的对现金的占有。这种多义性直接导致了存款占有归属认定上的不确定性,从法治国原则的角度来看这将对法安定性与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构成威胁。因此在刑法教义学上,自上,有必要讨论这种多义性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德日刑法教义学传统中对于财产犯罪基本概念的解释;自下,则应着眼于这种多义性在现实案件处理上的必要性与妥适性。本书尝试从清理我国刑法中涉及存款占有这一命题的具体案件出发、结合德日刑法理论和实务对于这些案件的处理讨论存款的占有所具有的这种多义性在教义学解释体系和实践处理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财物概念上主张有体物概念,在占有概念上主张事实上的对物的控制支配,以这两个概念为基点主张存款的占有应以现金的事实占有为出发点来解决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
淘宝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38n.10677092.0.0.11891debVOFP4X&id=571973078128
微店链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5537817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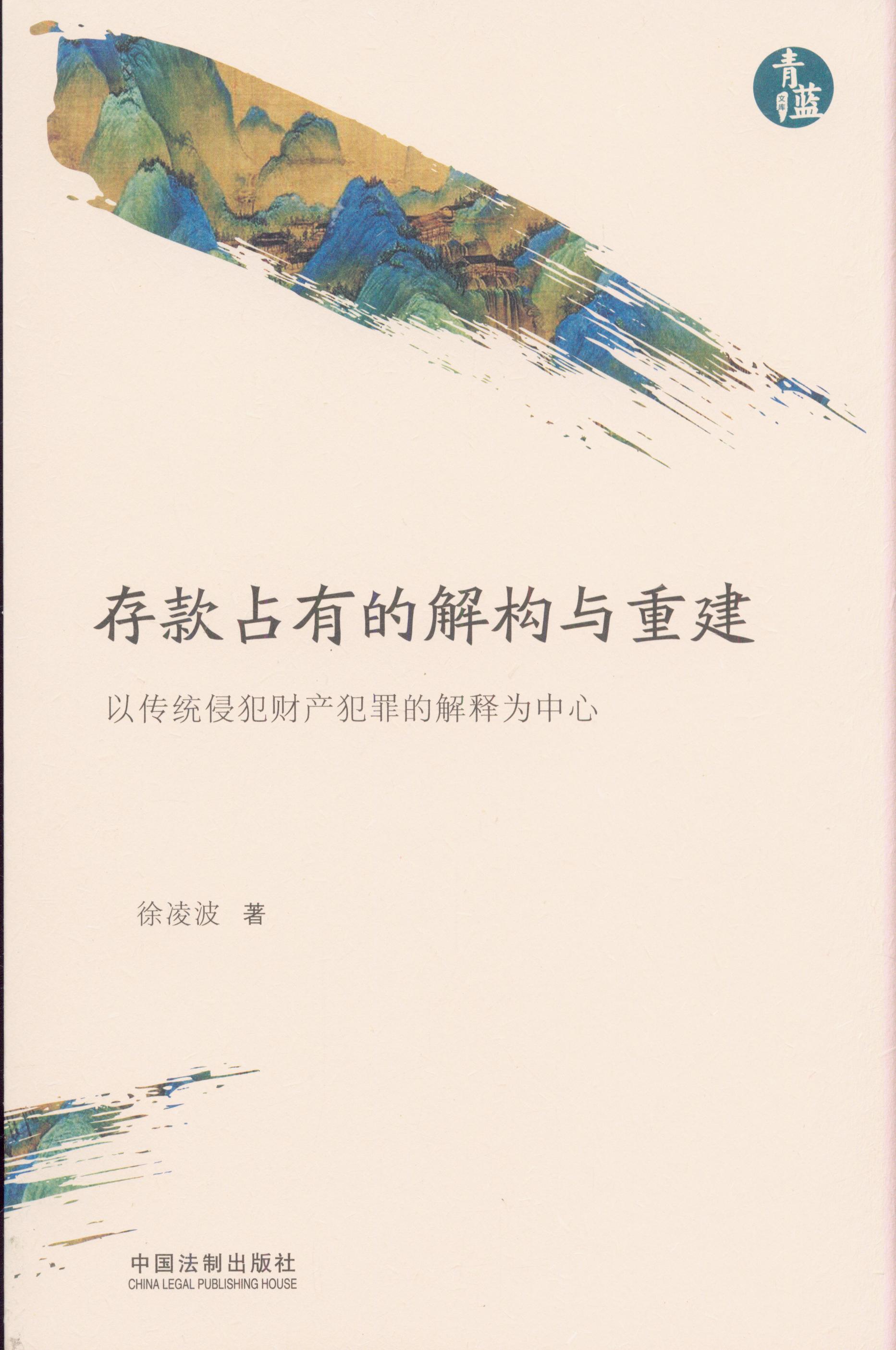 首先,存款债权的特殊性体现于我国刑法的明文规定之中。《刑法》第9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从条文表述看,刑法将公民储蓄视为公民“所有”的财产,与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其他生活资料置于同等的地位予以规定。尽管在这里使用了“所有”一词,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刑法认可了公民私人对存款的“所有权”,而应当理解为我国刑法上对于公民的存款债权给予了特殊的保护。笔者以为,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而非构建财产权利归属的等级和秩序,因此,就财产权利的区分与体系构建应当尊重民法上的规定,这不仅是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考虑,也是基于效率的考虑,在民法之外重新在刑法上构建新的财产权利体系,不仅浪费理论和思想资源,同时也容易导致讨论上的混乱而必须不断地重新对相关的权利进行重新定义。
首先,存款债权的特殊性体现于我国刑法的明文规定之中。《刑法》第9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从条文表述看,刑法将公民储蓄视为公民“所有”的财产,与公民的合法收入、房屋、其他生活资料置于同等的地位予以规定。尽管在这里使用了“所有”一词,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刑法认可了公民私人对存款的“所有权”,而应当理解为我国刑法上对于公民的存款债权给予了特殊的保护。笔者以为,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而非构建财产权利归属的等级和秩序,因此,就财产权利的区分与体系构建应当尊重民法上的规定,这不仅是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考虑,也是基于效率的考虑,在民法之外重新在刑法上构建新的财产权利体系,不仅浪费理论和思想资源,同时也容易导致讨论上的混乱而必须不断地重新对相关的权利进行重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