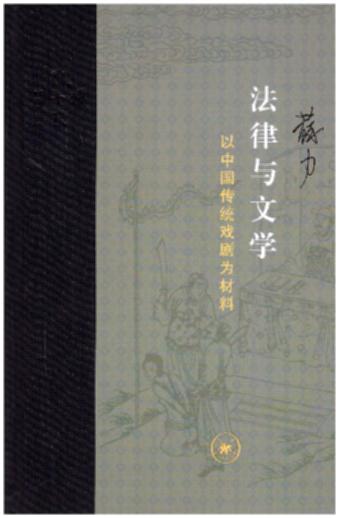
附录1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
法的关系……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
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
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
一
我从近年中国的两部颇为上座的、反映当代中国农村法治建设的电影谈起。
第一部电影是《秋菊打官司》,讲的是西北农村中的一个纠纷处置(而不是解决)。为一些并不很紧要的事,一位农民同村长吵起来了,骂村长“断子绝孙”(村长的确只生了四个女儿)。这种话在中国的社会背景(尤其在农村)下是非常伤人的。愤怒的村长和这位农民打了起来,向村民的下身踢了几脚。村民受了伤。村民的妻子——秋菊为此非常愤怒。她认为,村长可以踢她的丈夫,但“不能往要命的地方踢”。她要讨个“说法”,大致是要上级领导批评村长,村长认个错。由于这种纠纷在中国农村并不少见,而且伤害也不重,因此乡间的司法助理员没有给予这位村长正式的处罚,而是试图调解一下。调解不能令秋菊满意,于是她先后到了县城、省城计“说法”。经过种种努力,最后在一位律师的帮助下,上级派来了公安人员调查,发现该村民受到了轻伤害(但不是下身受到伤害),加害人应当受到治安处罚。村长被处以15天的行政拘留。但在告知秋菊这一决定、村长被带
走之际,秋菊说,怎么把人给抓了,我只是要个说法。她站在村头的公路笾,看着远去的警车,满脸的迷惑不解:为什么法律是这样运作的? 第二个电影是《被告山杠爷》。简单说来,山杠爷是一个非常偏远的、据说治安秩序很好的山村(县乡的治安人员都从来没有来过)的村党支部书记。他个人品质很好,非常受人尊敬,但他的职责和品性也使他与村里的一些人不时发生冲突,有时他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合法的手段,强迫村民。村里有个年轻媳妇虐待婆婆,甚至打伤了婆婆,受到了全村人的谴责。山杠爷看不过,在该媳妇屡次打骂婆婆的情况下,命令人把这个媳妇抓了起来,游了村。游村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民间惩罚方式。羞愧和愤恨之下,青年妇女跳河死了。事情捅到了上级司法机关,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
这里的介绍当然是大大简略了,电影本身包含了更多的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信息。对于这两部电影,不少中国法律人和评论家的解释是,它们反映了中国正在走向法治,人民群众已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2]然而,这两部影片(尤其是《秋菊打官司》提出的问题很多,底蕴很丰富,显示出“形象大于思想”的特点,因此任何理性的解释在对于形象的直觉感悟面前都往往显得简单、枯燥和拙劣。尽管如此,理智的、叫真的追问却可以使那些不明确的、也许是一闪即逝的感触得以明确和确定,使那些让我们动情的东西以思辨的形式昭示于人间。
当然,本文不可能、也不准备对影片的内涵作全面分析。本文将集中讨论:当我们看到一种据说是更为现代、更加关注公民权利保障的法治开始影响中国农村时,究竟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种“现代的”法治在他们那儿能否运行,其代价是什么?
二
就本文的实质性问题而言,这两部电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无语境的、客观普遍的权利,可以毫无疑问地据此建立一个普适的法律制度来保护这种权利。通常的观点,以及这两部电影所展现的法律实践中隐含的观点,都是一种普适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存在这种普适的权利界定,特别是在一些西方学者通常称之为基本性的权利上:安全、自由和财产权。尽管这种基本和非基本的权利分类在理论上早就受到质疑,但在实践上仍然很有影响,包括在当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当代中国的正式法律和法律运作都受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
但是,就秋菊的案件来看,这种观点有很大缺陷。例如,秋菊说,村长可以踢她丈夫,但不能踢她丈夫的下身,这种关于权利的界定明显不同于
法学界的权利界定。又例如,尽管正式的法律没有规定,但在中国农民和许多城市公民心目中,都会认为骂别人断子绝孙(哪怕说的是事实)也是对他人的严重伤害,这种伤害甚至要比某些身体伤害更为严重,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侵犯。然而,我们的正式法律制度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是依据那种进口的观点构建起来的,因此,身体的伤害是伤害,而语言、至少“断子绝孙”这样的语言不构成伤害。
当然如果仅仅是伤害分类不同,或这一分类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那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语言具有构造现实、影响现实的力量,特别是法律的语言。伴随这种定义和分类而来的是一个正式法律的运作逻辑及其带来的社会效果。在《秋菊》的纠纷中,当司法机关没有发现秋菊丈夫受到身体伤害时,正式法律就将这一纠纷推开;而一旦证实有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时,伴随的则是法律上的行政拘留——行政拘留被认为是恰当的、合理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而没有给予秋菊所要求的“说法”。甚至这个正式
的法律制度无法理解、也没有试图理解什么是秋菊要的“说法”。我说的是这个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运作者;其实这个制度中的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知道秋菊的“说法”大致是什么;仅仅因为在这个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没有这个“说法”的制度空间,因此无法理解“说法”这一不合所谓的现代法治模式的请求。[5]换言之,只有符合这一法治模式的请求才构成诉讼请求,才能进入这一程序。在这里,制度的逻辑限制了一种人人知道的知识以及其他可能性。如果不是将法治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话,应当说,在这里,实际就是法治——规则在统治,而不是人们以他的私人知识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裁决,即使这样的裁决是合乎情理的。[6]
必须承认这种法律运作作为制度的合理性。我并不仅仅因为这一个案子的得失就主张回到那种由某个圣明智慧、公正廉洁的个人依据个人洞识恰当处理个案的人治模式;那样的人治可能会产生完美的结果,但——即使裁决者个人品质无可指摘——也完全可能产生暴政。从长远看来,从发展趋势和社会条件来说,中国都必须建立制度化的法律,建立法治。但我们知道,任何制度性法律都不可能完满地处理一切纠纷,都必然会有缺憾之处。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法律制度具有总体上的合理性。的确,对于许多受过正式法律教育的人(包括我自己)来说,可能都会认为,正式的法律制度更为正义,更具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正式的法律制度没有改进之处。因为正义和合理性并不是大写的。借用麦金太尔的一部书名,那就要问一问“谁家的正义?何种合理性?”。如果 按照那种普适的、客观的权利观和法律制度,权利和权利保护都将以一种外来的观念来界定,而对于人们的“地方性知识”(再借用吉尔兹的一部书名)却没有给予多少重视。
必须指出,我并不反对吸取西方的观念和法律制度,我主张对任何观点都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然而我的确对那种大写的普适真理持一种怀疑,因为这种大写的真理有可能变得暴虐,让其他语境化的定义、思想和做法都臣服于它。在近现代历史上这种经验教训并不少见。[7]
就秋菊的情况来看,秋菊的要求更为合乎情理和可行,而且其社会后果也更好一些。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从这个角度看,界定权利和建立权利保护机制的权力应当是分散化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考虑当事人的偏好,而不是依据一种令人怀疑的普遍永恒真理而加以中心化。因此,至少从秋菊的困惑来看,我们应当说,中国当代正式法律的运作逻辑在某些方面与中国的社会背景脱节了。
持这一立场并不必然意味着我完全同意秋菊的权利界定。我可能不同意。但假如可以发现我的观点更接近那个大写的真理的话,也许可以把我的观点强加他人,但问题是至少目前的研究表明不存在这种符合论意义上的真理,[8]那么,也许我们应当考虑的就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哪一种定义和权利保护机制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均衡了相关各方的利益。
摘自:《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精)》,苏力著,
内容简介:试图拓展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法律与文学。我将主要以中国的一些传统 戏剧为材料,分析法律的或与法律相关的一些理论问 题。
尽管运用的材料是文学的、历史的并因此是地方性的,我的根本关切却是当下的、现实的因此是一般性的。这种关切表现为,首先,我试图从理论逻辑上 阐明——而不是传统的“讽喻”或暗示或影射——这些问题对于今天中国法律与秩序之建构形成的相关性 ;其次,在这一努力中,我希望创造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作为法学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支的可能,以及更一般地——与我先前努力一致——创造在中国思考我 们的、同时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问题的可能性。前者关注的是法律制度;而后者关注的是法律理论。
微店链接:https://weidian.com/item.html?itemID=214958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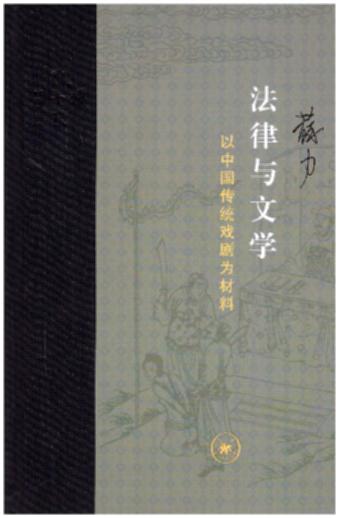 附录1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
附录1 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