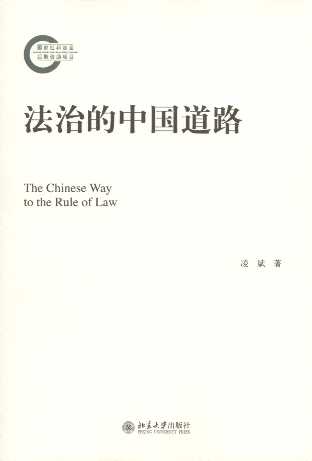
法治的中国道路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法治的专职主义和群众路线这两条路径并行相悖。两条法治路径在理念和实践上的二律背反,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基本特点,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问题意识
凌斌
多年以后,每当回想起那个在其他国度也许不可思议、但在当代中国却司空见惯的一幕,我仍会感到深深的触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盘坐在新华书店的法律专架下,寻章摘句地抄写着一些法律条文,一行行蝇头小字如同她额头上深深的皱纹。
那时萦绕心间的,不是老人的善恶,案件的是非,也不是我的怜悯与同情,而是这样一个“超善恶”的实践问题:如果中国的普通官民大都像这位老人一样,不相信律师和法官,而是相信自己可以直接理解和掌握法律,这对中国的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意味着什么?
普通的官员和民众是法律外行,但并不是孩子。我们没法用一句“法盲”,就打发掉所有问题。强迫他们放弃原本的生活理想,强迫他们接受并不喜欢、并不理解甚至根本并不了解的陌生理想,结果只能是导致更多的怀疑、隔阂和抗拒。毕竟法律人勾勒的法治图景还没有到来,对许多普通官民来说,那也许是另一个乌托邦。
普通人对法律人的不信任和对自己的自信,也最终影响到了法律人本身的职业伦理和制度理念。具体的行为特点和改革措施不论,就是“大调解”、“大信访”和“能动司法”这些整体性的法治理念,一定程度上也都是对这种现实处境的实践回应。这就是法治建设的困难所在。
立法之后的法治难题
立法之后如何实现法治?法治如何取信于民?这个立法之后的法治难题,也就是法治的道路选择问题,其实是人类第一次探索法治实践时就已然而且是必然会提出的问题。
整整十年之前,当我偶然读到《商君书》的《定分》篇时,我第一次明确意识到,早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商鞅变法”之初,当时的立法者秦孝公已经十分迫切地提出了立法之后如何建立法治的实践难题。这就是本书所谓的“孝公难题”: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
法治的“孝公难题”,开启了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法治之门。随着对中国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出土典籍乃至古史传说的了解,我终于意识到:原来最早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崛起大国中实现法治的,是中国;原来最早提出法治道路的选择问题的,也是中国。原来,人类最早的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的创建者,竟然是那个千百年来被视为专制残暴、刻薄寡恩、最终作法自毙、身败名裂而为现代法律人所深深不耻的法家人物商君公孙鞅,和那个野蛮秦国的中兴之君、虎狼之师的始作俑者秦孝公渠梁。
商鞅变法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法治经验。《史记·商君列传》用两则事例,“南门立木,以明不欺”、“太子犯法,与民同罪”,记录了这位法治前辈的智慧、胆识、魄力与决心: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鞅新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最终通过“为法令为禁室”和“为法令为法官”两个具体措施,通过专职法官垄断法律传递和法律解释的司法制度,实现了从立法到法治的转变。
我们这些站在现代立场上的法律人,可以凭借自己的道德优越感,鄙薄商鞅的严刑峻法、刻薄寡恩。然而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两千年来,这样的法治理想,有几时能够做到?又有谁能够重建一种上下不欺、民心大悦的法民关系呢?不要把困难都推给技术和观念。当时有当时的困境,今日有今日的便利。
实际上,商鞅变法留下的也是中西共通的普遍经验。西方法治建立之初,面对的是同样的“孝公难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至上权威,作为司法公信和法治信仰的顶峰,同样不是从来如此。正如布雷耶大法官所说,“在美国不同历史阶段,最高法院的判决都曾经遭遇社会各界,甚至总统、国会的抵制、反对与忽略。”学界的以往研究,多是聚焦于当代西方的法治成就。因此往往关注现阶段的“同时比较”,而忽略了类似历史时期的“同期比较”。相比于西方法治的当下发展,我们更应当重点考察那些与当代中国处境相似的“法治转折”时期,考察其建立司法权威和法治信仰的历史过程。
某种意义上,古今中外的法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回答“孝公难题”的历史。立法之后如何实现法治?这样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秩序,这样一套高度复杂并且溯及既往的规则程序,这样一个旨在重新规定行为模式、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的历史进程,如何能够获得普通官民的接受和服从?这一问题,其实是一切通过法治改造国民的社会变革都必然遇到的现实挑战。
法治路径的道路选择
古今变革,呈现为法治的两条路径。法治的道路选择,就是在这样两条路径之间作出判别和取舍。本书将前述的法治路径视为两种“理想类型”,而将法治道路作为这两种理想类型的某种实践混合。有时,法治的道路可以清晰识别为某一条法治路径,有时则是两条法治路径的相互重叠。
因此,本书首先区分和描述的,就是这样两条并行的法治路径,这样两种对立的法治理念:一条路径是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奉行的由专职法律人士垄断和掌握法律的“专职法治”,奉行的是“法治的专职主义”;一条路径是当代中国独有的“民本法治”,追求以普通官员和一般公众能够直接理解和掌握的方式制定、执行和解释法律,贯彻的是“法治的群众路线”。中国的法治道路所面对的路径选项,尚且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法治的中国道路,是群众路线与专职主义这两条路径相互交织的法治道路。
法治的专职主义,是从顶层设计出发一举奠定法治的伦理基础,自上而下一劳永逸地从整体上尽快确立政府信用和法律权威。这往往需要商鞅式的暴力强制,用平等、民主、开放的程序正义以及铲车、水枪和手铐的暴力机器,建立法治的权威。法治的群众路线,是从底层基础出发逐步积累法治的伦理资源,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从个案上逐渐培养司法公信和法治信仰。这就需要从秋菊式的诉求出发,用外行听得懂的和能接受的道理,走群众路线,将人民利益看得和宪法法律一样至高无上,将代表人民利益和实现宪法法律的党的领导,看得一样至高无上。法治的专职主义,因此更为依赖国家暴力和顶层设计,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强制变革。而法治的群众路线,则需要追求宪法法律、人民利益和党的领导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
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正是摇摆于两条并行相悖的法治路径之间。法律人也因此分裂为商鞅派和秋菊派,都要把中国的法治进程拉向自己钟情的路线方针。法治的两条路径不仅表现为法律书架下自学老人的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而且始终伴随着法律人自己的困惑与迷茫、无奈与坚持。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基本特点,就在于法治的专职主义和群众路线这两条路径并行相悖。两条法治路径在理念和实践上的二律背反,构成了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基本特点,也构成了本书研究的问题意识。
本书并未刻意化简这一中国法治的基本困境。相反,本书的主旨在于,中国法治道路的内在动力就在于其基本困境,就在于两种法治理念的对立统一,两条法治路径的二元变奏。因此首要的问题不是急于选定立场,而是尽可能充分呈现这一法治困境的根本性、复杂性与普遍性,呈现这一法治难题的当代特点和历史渊源。只有充分认清问题的实质所在和困难所在,才可能正视和解决真正的问题。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问题会因此变得易于解决。这只是意味着,认清现实,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本文为《法治的中国道路》序言)
摘自:凌斌 著 《法治的中国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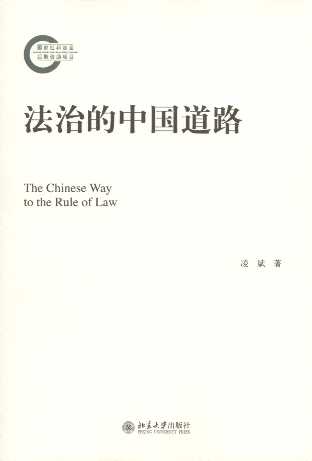 法治的中国道路
法治的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