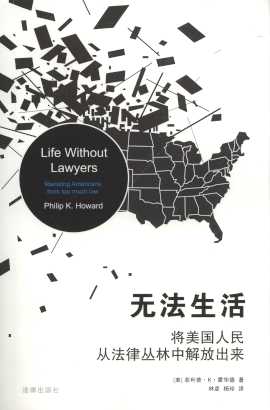
反思权威
没人想重新回到旧时代,那时我们给予残障和精神障碍人士的待遇可被形象地描述为“眼不见,心不烦”。我父亲得过两极型忧郁症。当我十来岁时,他被关在东方州立医院——肯塔基州的一所精神病医院。当肯·克西(KenKesey)的《飞越布谷鸟巢》(One只Pw over’the Cuckoo’J。Nest)出版时,书中的情节对于我来说早巳熟知。这是由于我造访东方州立医院的经历——我父亲经过电休克疗法后死人般的表情,以及游荡在肮脏的环境中那些尖叫的人们。幸亏现在我们对责任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绝对权利的替代品并不是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人类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即把选择看作非黑即白的事。但权威结构可能远远没有这么简单。立法机关可以确立清晰的公共目标,它们能授予官员们实现这些目标的职责,权衡所有选民的需求。它们能提供资金,它们能授予其他官员监督职责,包括监督责任的落实情况。但是,实现这些目标仍然要求现场决策——譬如,决定某一学生是否太暴力而不能和其他学生在一起学习。
与风险一样,权威是人们并不想谈论的主题之一。但是,在任何一项共同事业中,人们都必须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并不是由确保智慧和公平的神奇机器所产生的,而是由那些具有职责的人——普普通通的人所做出的。我知道这是个坏消息。可能是更坏的消息,正如哈夫曼勋爵阐释的,那些由掌权者所做的决策对于我们的自由而言是必需的。如果法官们不对作为法律问题的合理风险划分界限的话,那么不久以后法律恐惧将侵蚀我们的自由。湖泊和河流将不再向公众开放。如果缺乏平衡不同利益的权威,公平同样是不可能获得的。
人们将不可避免地犯错误,或许情况还会更糟。有些法官可能并不明智;有些教师可能并不公允;有些经理人可能是自私的。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他们将被权威链条的上级要求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人们也可能做出好的决定。乔治·华盛顿对于试图过度控制官员的决策保持谨慎。“没有人比我更倡导适度的限制”,华盛顿说,“但是我至今还无法……在人们提供必要服务所需的权力中找到它的恰当位置,如果仅仅因为他们存在做错事的可能性的话。”
然而,常识正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价值压倒事实,而对权威的不信任又是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美国人认为自由意味着通过抵制权威来保护人民。这是我们的不同政党存异求同的地方,他们都竞相创设出制度以有效地阻止任何掌握权力的人做出决策。
自由主义者关注个人所面临的困境并相信个人权利是确保公平的最佳途径——任何认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必须有权运用法律质疑掌握权力的人所做出的决策。正如法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所言,“‘权衡的’(balaIlced)是‘被否定的’(denied)的代名词”,因为(权衡的)结果系于“那些掌权者”的决定。
保守派的意识形态是明确地构建在对政府权威的不信任上的。罗纳德·里根曾说,“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英语语言中最令人恐惧的10个词就是‘我是联邦政府派来的,我是来帮你的。”’如果必须制定管制规章,那么就制定尽可能细化的规则;保守派们当然不想让政府官员自由地行使决策权。当认为法官在干预他们的价值观时,保守派们是会发怒的。他们会认为那是“司法能动主义”。在他们看来,法官就应当机械地适用法律。
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对权威的不信任发端于光谱中相反的两极,自由主义者不信任商业,而保守主义者不信任政府。但久而久之,这种区别已经变得模糊了。法律桎梏现在成为针对任何掌权者的一种条件反射。
事实上,美国至今尚未悟出权威与自由的合理关系。贯穿我们国家的历史,美国人始终认为权威是自由的敌人。我们建国元勋们的第一次尝试——《邦联条例》,由于缺乏权威无疾而终。第二次尝试——《联邦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和个人一些保障以抵抗政府权力。但是,这些元勋们所处的农业社会并不要求政府拥有除了基本的打击犯罪、保障合同和州际贸易以外的其他权力。
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变得更加相互依赖,而私人权力的滥用也变得更加危险。但是,我们固有的、反对政府权威的僵化意识形态——自由放任主义的主要教条——使我们根本无法对付工业资本集团滥用权力。这个时期的联邦最高法院,听起来像是爱默生的信徒,鼓吹着个人自由的胜利号角:
“【一个人必须自由地】在不干涉其他人平等权利的情况下行事,让他的自由判断能够主宰其对自身幸福的追求。也就是说,自由地追求那些最适合自身能力培养的职业和副业,并且能够最大限度地乐在其中。”·
这些自由宣言非常鼓舞人心——至少如果能将其适用于垦荒农民或者想开一家店铺的商人的话。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却用这一理念撤销那些为保护工人安全而起草的法律,明目张胆地维护工业资本集团的自由。允许一个工厂主“让他的自由判断能够主宰其对自身幸福的追求”而压榨工人,这可能并非爱默生所说的自由。
如今,我们将那些得意洋洋发表的有关自由的言论当作一个残忍的笑话。在雅各布·里斯等进步主义者领导下所展开的为争取人性化工作条件的斗争几乎与半个世纪后为民权所展开的斗争一样艰难。这一姗姗来迟的转变呼唤着一种新的法律哲学。
自由不能仅仅被界定为为抵御政府权力而提供的保障。人们同样需要保护,以免受商业(集团)的侵害。我们不仅没有正视权威与自由的联系,反而建立起了进一步削弱权威的制度。随着20世纪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权利革命之后,自由被重新定义为为抵御一切权威(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而提供的保障。诸如正当程序这样本来用以对抗政府权力而存在的宪法保障,现在被适用于学校和工作场所中普通的人际关系。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对任何决定提出挑战。
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和个人权利的哲学都被塑造成为对抗权威所提供的保障。明显的以对抗政府为宗旨的自由放任主义导致了工厂主的暴政。以对抗任何权威为明确目标的个人权利则导致了愤怒的个人暴政。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自由都沦为了牺牲品。
权威并非自由的敌人,而是其保障。法律不应当将剑指向权威。法律应当被用来界定合理权威的边界。这一功能是通过维护划界的权威来实现的,而其所划的界限将确定我们自由的空间。权威当然可能被滥用,但是将权威让渡给那些没有公共职责的人则是滋生权利滥用的配方。
摘自:(美)霍华德著《无法生活:将美国人民从法律丛林中解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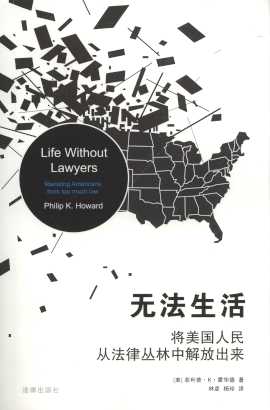 反思权威
反思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