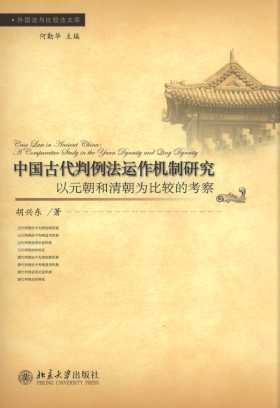
元朝判例的司法功能
元朝判例的司法功能受制于其整个法律制度的设置,由于元朝法律渊源主要是判例法,所以判例在司法中的功能基本上是作为法律渊源。当然,由于元朝存在制定法,有些判例是作为对制定法的解释与补充而存在的。此外,中国古代法律渊源自春秋以后就有很强的制定法倾向,所以元朝在大量适用判例的同时,很多时候通过判例进行立法也成为判例的重要功能之一。从元朝总有把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成文化倾向看,元朝虽然承认并大量适用判决法,但它还是受制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
一、作为唯一法律渊源
元朝判例在司法中的功能与清朝等有成文法典的时期相比,其特点之一就是大量判例直接作为案件判决的法律渊源。元朝判例作为直接适用的法律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非常明显。至元七年八月南京路息州民户丁松诉妹妹定奴在丈夫死后守志不嫁,夫家不令归宗案在判决时直接适用了先例赵义女儿青儿丈夫死后守志,夫家不愿归宗案。此案从判决的法律依据看就只有唯一的先例。①此处先例是作为法律来适用的。另外,延事占五年十月婺州路兰溪州同知亦不刺金收受姜正四中统钞五定,在没有案发时就退回赃款。“亦不剌金招伏,依不枉法例,合决五十七下,殿三年,注边远一任。”但由于此官员在任宜兴路同知时就因收受僧无聚中统五定,听到事发,主动把钱还给事主周僧判,因此被判“比例减二等,断讫三十七下,解(见)[现]任,别行求仕”。对于现案中是否要依再犯加重处罚,地方官认为是个疑难问题,“若拟再犯不叙,终是先犯减等断罪解任别叙,缘系为例事理”。于是呈送刑部裁决,刑部检查出延袼元年九月松江府推官郑鉴在任庐陵县尹时曾取受萧保一嫂钞十定,知道事主要告发再退回赃款,判决被减二等,笞四十七下,解除现职,调任他处。此时又收受薛元二行贿至元钞二定,判决时“依不枉法例,杖六十七下,殿三年,降一等”,理由是“本官职役若拟再犯不叙,终是先犯减等断罪解任别叙,缘系为例事理”。考察了先例后,刑部直接适用先例判决,“兰溪州同知亦不剌金,先任宜兴州同知,取受僧元聚钞定,闻知事发,回付过钱人周僧判收接,依例减罪二等科断,今次受要姜正四钞五定,若以再犯不叙,缘先任取受闻知事发回付,罪既不曾全科,即与松江府推官郑鉴所犯一体,以今犯定论相应”①。此案把先例松江府推官郑鉴案作为判决的法律渊源。
二、作为选择适用相关法律的理由
元代判例适用上有时是作为适用成文法的理由或依据,因为先例在事实上解决了成文法的不足与缺陷,让成文法适用于具体案件更加明确与具体。
元代把判例作为适用法律的理由时,有时是通过先例认定案件的性质,以便相关法律的适用。延{;占六年十二月嘉兴路贼人钱阿添于延{右四年四月十九日夜盗沈世明钞定、银钗等物,五月二十日又偷盗忽都不丁银器等物,被捉拿到官。浙西廉访司分司判决刺左臂,杖断一百七下,配役三年。该犯在发配路上逃走,并自己除去刺字。该
犯在延袼五年四月初五日夜再次偷盗他人财物被拿获到官,对其第二次犯罪是否适用再犯偷盗拟出军上出现了法律问题。因为相关法律是指被配役结束后再犯者判出军,此犯在没有到配役地就逃走,故存在是否属于二次犯的问题。为此送刑部裁决,刑部在判决时适用了李黄再犯偷盗李阿颜钱物案,不加重处罚,仍按初犯处罚。这时刑部就把先例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奉此本部议得:贼人钱阿添所招,若以再犯定论,缘先犯终是未到配所,止据今次不合偷盗事主哈只家财,估赃至元钞一百贯之上,比例杖断一百七下,刺右臂,徒役三年,满日充警相应。”②从此案看,判例主要是作为认定此案中人犯的行为是初犯还是再犯性质的依据。从法律适用看,此处判决适用的是初犯偷盗法,而不是再犯出军法,但不管是偷盗初犯或再犯在处罚上都有相应法律规定,先例仅作为选择适用不同法律的依据。
元朝在人命案中有特别规定,那就是都要征偿烧埋银,并且人犯若遇到大赦被免除刑罚后要加倍赔偿烧埋银。这一规定没有作出任何例外规定。现实中,出现在戏杀时若遇到以上情况是否同样适用此法的问题。延{;占六年十二月饶州路发生了贩卖干鱼的李高三、余兴二与李杞一嬉戏,致李杞一死亡案。案发后遇到大赦,对李杞一是否要加倍征偿烧埋银上存在争议,行省理问所认为应加倍赔偿,行省却认为不应加倍征赔。当时拟判是:
本省议得:李高三等作戏致伤人命,别无故犯情意,罪合徒刑,钦遇原免,如于各人名下均征中统钞一十五定,付尸亲。理问所比依省部已断徐咬住、王狗儿戏杀例,合征烧埋银两,各人罪止徒刑,钦遇释免。若拟倍追,终无所守通例。可以看出,判决时适用了先例徐咬住、王狗儿戏杀人案。先例在判决时不加倍赔偿的理由是戏杀在法律上仅处以徒刑,与其他形式的人命案不同,所以遇到大赦时亦不加倍赔偿。刑部在判决上支持了行省的拟判,否定了理问所的判决。从另一角度看,先例仅是作为适用不加倍赔偿法的依据。
送据刑部呈议得:李高三、余兴二所犯,止是用言作耍,拦当李杞一不容小遗,以致跌伤身死,中间别无故杀情节,又非以力共戏,罪遇释免,所拟烧埋银两,如准本省所拟,李高三等名下均征中统钞十一定给付苦主相应。①
此案在适用先例时主要是作为适用征赔烧埋银要增倍的理由,而先例徐咬住、王狗儿案是戏杀,与此案在性质上一致。此外,两案在处罚时都遇到大赦,所以相关赔偿上以先例作为依据,因为征赔烧埋银是有法律规定的,所以先例仅是如何适用征烧埋银法律的依据。
大德四年四月肇庆路高要县发生朱聪纠合郑宥一偷盗陈成中家黄母牛一头宰杀,遇到大赦,对人犯是否要刺字和征罚双倍赔偿上没有相关法律,不知如何判决,同时,遇赦时虽然对人犯处以轻刑,但不是全部免除处罚。刑部在判决时,认为刺字应按中统五年八月初四日的法律,即“中统五年八月初四日钦遇圣旨条书一款(云云见警迹人类)”①;在要不要加倍赔赃上,有先例是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河南行省贼人张和盗马一匹在正赃追回后,倍赃还没有赔时遇到赦书,“将本人刺断陪赃,追征间钦遇诏书,检会到至元二年三月钦奉(云云见前无偿折庸类)”②。刑部根据以上法律对张和盗马案正赃依法追还原主,倍赃则是遇赦不再征罚。“张和盗马一匹,照依钦奉圣旨
条书合追正赃,已行追给,所据(陪)[倍]赃,拟合钦依革废,如已追给本主者,别无定夺。”把法律与先例作为案件判决中法律适用的依据,判决贼人朱聪、郑宥正赃一定要赔,但倍赃则免除,刺字依法进行。“科断盗贼,皆据所盗正赃断罪,仍追(陪)[倍]赃,盖为情理难容,今既遇恩,本罪得减,正赃无问费用,见在全追给主,不曾随罪减征,外据(陪)[倍]赃,即非元盗之数,如蒙免征,依例刺字相应。”⑧从此案判决看,先例作为在遇赦时是否要倍赃的法律依据,其实是对相关法律的确定。
有时适用先例仅为了解决管辖权上的问题,而不是实体法上的问题。如延袼三年四月李饶等告建昌州茶提举司司吏袁莘等贪污受贿案,但他的上司占悟却不让有司管辖。④为此行台提出按“若依饶子才告晏提领取受例,从行省委官与廉访司一同追问”。御史台依据大德十年五月朱仁诉谈提举等西蕃茶提举司官员贪污受贿案。而这些西蕃官员提出自己不受行台管辖。“他每说道:‘俺的勾当其问不拣谁休入来者’,么道”⑤,御史台为此奏请皇帝裁决,回复是此类案件由御史台管辖。这样本案解决了此类问题的司法管辖问题。此案中建昌等西蕃地方少数民族头人在做茶叶提举司官员时贪污受贿,想抵制监察御史的管辖,认为自己由宣政院管辖,而本案通过适用先例解决了管辖权上的问题。
从上面的个案看,先例有时仅作为相应法律适用的依据,并不全作为法律渊源使用。
三、作为相关立法的依据
元代使用先例有时不是为了司法,而是仅将其作为立法的依据。通过相应先例提出立法或说明立法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是元代判例的司法功能之一。至元二十九年邵武路总管府总管提出“禁乞养异姓子”立法时就使用此种方式。邵武路为了说明此立法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引用了发生在该路异姓养子出现问题的具体案件作为依据。此案是异姓养子黄云瑞因风水及财产问题而挖掘祖先黄百十三坟墓。
今与本路总管府官一同讲究得:父子嗣续人伦大本,同宗继绍,气脉感通,非我族类,神不歆享,私立异姓,徒启祸源。如前弊俗,理宜更革,兼可预防,废乱户籍,潜息贩卖人口。准上禁治为便,牒可照验,备申行省照详施行。承此照得:本路近据录事司中解到同掘祖坟人黄云瑞,(贡)[供]得元系广西道宾州人氏,本姓陈,随姑陈氏嫁事黄千一将仕为无嗣子,立云瑞为嗣。于至元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妄以祖公黄百十三知府坟墓风水不利为由,令吴百七等将坟墓掘取讫棺内银器等物,及将尸骸烧化移于他处,却将元葬祖公坟墓山林卖与官将仕为主。罪犯招伏,审问(元)[无]异。看详黄千一将仕无子,不能于近族择有昭穆相当者立之,辄用其妻陈氏所携异姓孙改名云瑞,立而为嗣,族系既殊,情态少异,其间破卖田产,毁拆室庐,俱未暇论,最是乃祖黄百十三知府归土已三十余年,而黄云瑞乃敢盗发其坟,斧其棺,火其尸,尽取棺中元殡之物,至于坟莹庵宇,悉以售之他人。若使黄云瑞实系黄氏族党之亲,则知有祖宗骨肉,必不忍如此绝灭天理之事。此立异姓子者之明验也,乃至殃及九原,甚可哀也.。①
从上面引文可以看出,判例成为立法的依据。当然,由于此案的判例是立法的依据,所以判例与立法拥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延{右六年十月监察御史提出“逃驱偷拐钱物二罪从重论,免刺”的立法,刑部引用大德七年十月太原路贺来福偷盗本使耿忠银物案为据,此案按赃款数量应将人犯流远,但由于主人告免,被判杖断九十七下,依然为主奴。此先例被大德八年安西路李宝偷盗主人蛮子回回的财产案适用。上面两个判例作为刑部同意监察御史的立法的依据。因为李宝案中本应判流刑,但由于是偷盗主人的财产,改为杖九十七下。“拟合比例免流,依上断决九十七下,分付本使收管相应”。通过对先例的分析,刑部同意监察御史提出的立法。“今承奉本部再行议得:奴盗主财,并背使在逃,俱有断例。今后有犯,合准监察御史所言,二罪俱发,从重者论,与免徒刺相应”①。这里体现了元代立法上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元朝在判例使用上的特点。
此外,延祜七年二月淮西廉访司分司提出对革闲弓手祗候公开抢夺、骗取钱物行为应立法规范。立法动议提到刑部后,刑部对以往先例进行分析后,否定了制定相应法律的动议。为此刑部列举了至元二十四年八月南康路建昌县巡军张焦住强抢顾同祖钞一百五十丽案,被判“市曹对众杖断一百七下,刺字配役”;皇庆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湖广行省潭州路发生唐周卿、贾国贤公开抢夺蔡国祥棕帽案,帽上有红码脑珠子一串,白毡一个,判决“唐周卿所招,纠合贾国贤同谋强行夺抢蔡国祥棕帽,罪犯即与席驴儿一体,既已断讫,拟比依(切)[窃]盗刺字相应”;延{;占二年杨贵七抢夺案;延{;占五年云撇播诈取财物案等。因为每个案件的情节都不一致,所以“本部议得:公取(切)[窃]取皆为盗论,今淮西廉访司所言,革闲弓手、祗候人等执把器仗,拦截路行客旅,诈称捕捉逃军,辨验引据等项为名,强行夺骗钱物等事,若便议拟,中间各各情犯不同,难便定立通例,以[此]参详,今后此等贼徒,发露到官,招赃明白,比依前拟,临时量情刺断,其有司禁治不严,及不依例决遣者,验事轻重断罪相应”①。这里判例就是刑部不立法的依据。
元朝的判例适用形式上较为灵活,但都在法律意义上使用,因此它构成了元朝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自:胡兴东著《中国古代判例法运作机制研究/外国法与比较法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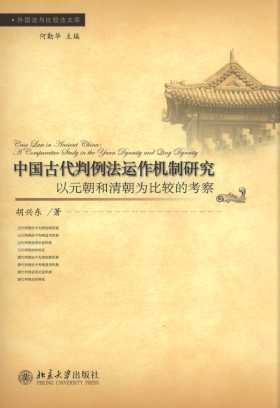 元朝判例的司法功能
元朝判例的司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