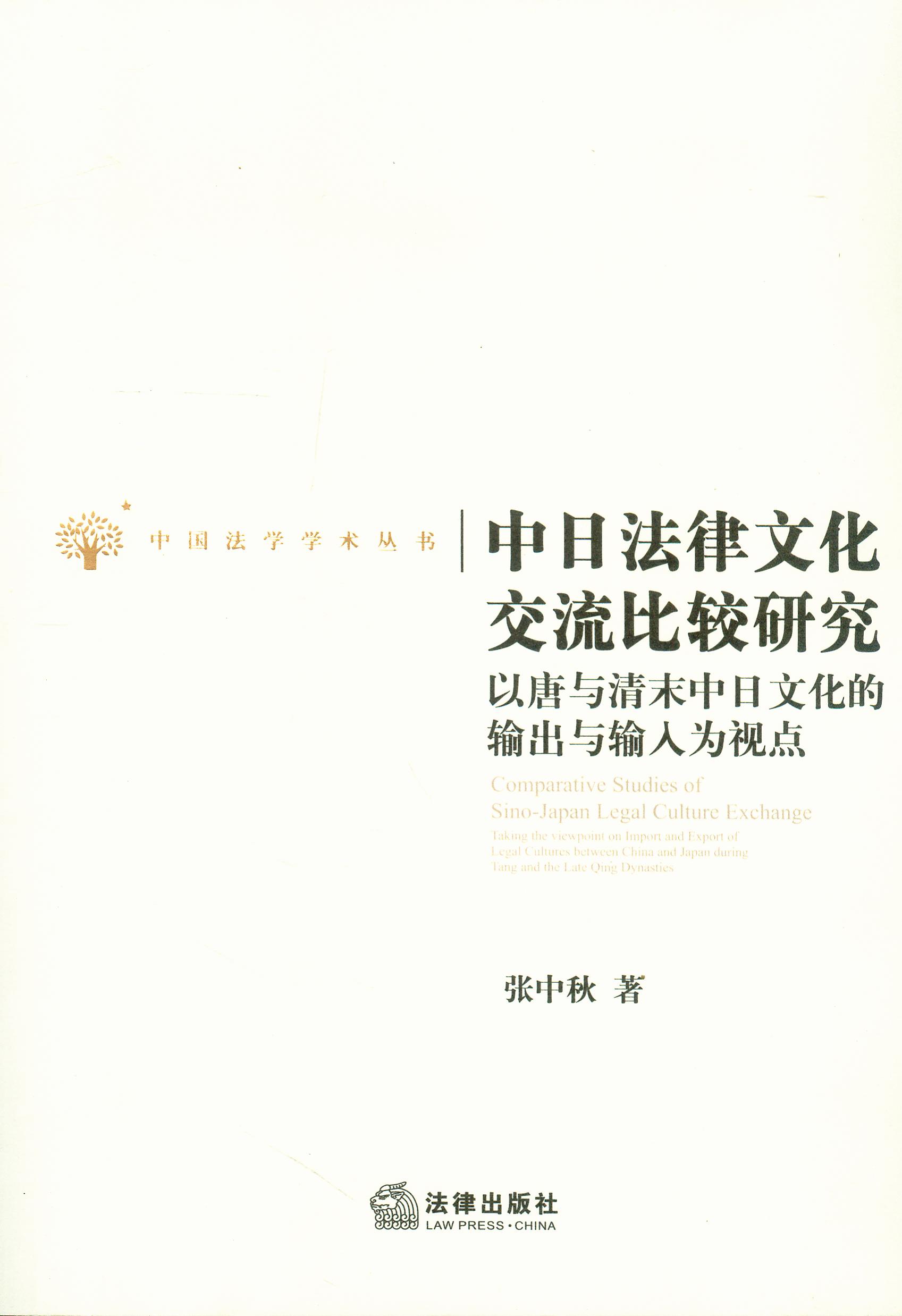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成败得失的人物观
在对法律文化交流的观察中,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被制度和事件所吸引,因为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但还有一些东西不能被遮蔽,尤其是那些在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事实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制度和事件的存废。笔者在整理中日两方面的资料时,一个极深的印象是,大化改新前后的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包括领导决策者和实际操作者,他们的经历、思想、心态和政治举措,都是有利于唐代法律文化的输入。如前所述,大化改新前日本的上层早已接触到来自中国的文化,并表现出异常的热心和钦羡。到圣德太子时,国家政治与这种文化(心态)结合起来,促成了他模仿中国确立文化立国的政治理想。为此,他依据儒家思想和经典,亲手制定了《宪法十七条》,为大化改新和唐律令的引进指明了方向。
大化改新的核心人物是中大兄皇子、中臣镰足和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曼,他们都富于儒学修养,熟知儒家政治经典,这在文化上和思想上保证了圣德太子所指明的方向的继续和发展。革新的公开领导人是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他们自幼博涉中国典籍,共拜当时日本的儒学大师南渊请安为师,向他请教“周孔之教”。由此,中国儒家政治思想被他们奉为圭臬。革新的幕后人物和实际操作者是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与僧曼,他们都是圣德太子在公元608年派往中国的留学僧。僧曼于公元633年回国,在华学习时间前后24年。南渊请安和高向玄理于公元640年回国,他俩的留学时间长达30余年。这么长的学习经历,使他们对隋唐中国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深入的认识,于是“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成为他们的共识。故而回国后,他们大都不再从事佛教研究,而是致力于传播儒家政治思想,推介隋唐政治制度。公元645年政变成功,孝德天皇即位,中大兄被宣布为皇子,中臣镰足为内臣,高向玄理和僧曼为国博士,由他们推行大化改新,领导日本走向模仿和追赶唐朝的法制社会。至此,对日本来说,引进唐代法律文化已没有任何政治和思想障碍,相反,一切都是有利的因素。
沿着圣德太子指明的政治方向和大化改新所确定的纲领,日本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唐化阶段,《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即是这一阶段的制度结晶。据日本史籍记载,(2)在《大宝律令》及其前身《天武律令》的修撰人中,伊吉博德曾参加过遣唐使团,萨弘恪为唐人,土部甥、白猪骨曾留学中国十余年;[’]调老人、黄文备、锻大角、山口大麻吕是大陆移民的后代,他们都有研读汉籍和中国法律的便利条件o[2]随后,《养老律令》在《大宝律令》基础上经多次删定而成,主事者主要有吉备真备和大和长冈。此二人都是留学生和遣唐使,在华18年(又说20年),遍学经史、法律、建筑等,是唐代法律文化东传日本的重要人物。对此,木宫泰彦先生说:
遣唐的学生和学问僧由于游学的处所不同,所学的内容也不同。……学生中最著名的是元正朝的吉备真备。他留唐十八年,学习经史,涉猎各种技艺。……专门学习法律的有大和长冈。他自幼爱好刑名之学,潜心研,后来和吉备等人入唐请益,颇有心得,当时凡习法令的都要向长冈请教。他还和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辨明轻重的舛错,矫正首尾的差异,这是人所共知的.
从公元604年圣德太子亲手制定并颁示《宪法十七条》指明政治方向,到中臣镰足等发动大化改新,再到伊吉博德、萨弘恪等制成《大宝律令》,最后由吉备真备和大和长冈等于公元718年删定成《养老律令》,前后一百余年日本学习、输入、吸收中国法律文化的线索清晰可见,其中起关键作用的领导决策者和实际操作者,他们的经历、思想、感情心态和专业知识,尤其是他们所处的位置和握有的权力,无不有助于日本对唐代法律文化的引进。对此,日本学者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可以附录在此供参考。
与日本大化改新不同,变法修律是清廷为应对最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而被迫采取的一项变革。这场危机最初由西方引起,但进入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东洋的日本加入了西方列强的行列,对中国形成了更直接巨大的威胁,甲午海战和《马关条约》让全世界看到了千百年来由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的逆转,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还没有把寻求“富强”的目光从西方移向东方的日本。八国联军、辛丑条约、庚子赔款等一系列的打击和失败,才促使西逃途中的西太后不得已下诏变法修律。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分析,开始时日本并不是中国变法修律的首选目标。这是自古以来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和文化交流传统的惯性所致。可以说,自中日交流以来,日本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有日本学者谓之册封体制的一部分,亦一直是中国文化的接受者,因此,在中日之间形成了压倒性的由中国流向日本的单向文化运动。中国长期视日本为“倭”、“夷”等这样带有轻侮性的称谓,反映了文化中心主义的优越自大,即使甲午战败,还是不能接受日本自大的“大日本”称谓。除却历史惯性和抵触心理外,实际亦是无知。自大和无知是满清统治者对列强冲击判断失误、行动迟缓的思想文化根源。因此,从咸丰开始到同治中兴的举措,实质是被动中的应对,与古代日本圣德太子决心面向中国学习的积极心态和远大理想不能相提并论。由此可以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日本大规模输入唐代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大化改新的政治成功和前此几十年就定下的基本国策之上的;而晚清没有这样的条件,领导决策者和实际操作者为此都缺乏必要的心理、思想和知识准备。
变法修律中的晚清政治格局形式上是慈禧与光绪的二元结构,[3]其实是慈禧支配下的一元体制。虽然大多数晚清观察家都承认,慈禧是新政的实际发动者,模仿日本变法修律亦是经慈禧同意的。但她的经历、知识和远见,还有她的年龄、精力和抱负,都无法与大化改新中的日本天皇相比。因此,有论者谓:“慈禧为人精明强干,意志坚强,具有统御和笼络群臣的绝大天才,自然毫无疑问。但她究竟只是一介女流,在当时礼教与传统的层层束缚下,她对实际社会的了解,实在有限,对近代世界崭新的情势,尤其缺乏深入的认识。她最大的关注所在,只在于如何保持清室的政权和她个人的权位,对于发展中国‘求强’、‘求富’的自强事业,她所着重的亦只是想阻遏洋人的深入侵略,纯粹采取一种消极性的观点,谈不上有何热心,更没有推动中国走上近代化的任何意识。”最后两句判语似乎有些绝对,西逃的屈辱和清室覆亡的危险使西太后对新政的态度比以前有了积极的变化,甚至亦不排除她希望新政的成功,因为新政有利于危机中她个人的权力和帝室统治的巩固。然而,这样的政治意图却同时严重制约了变法修律的成功。
比照古代日本的情形,晚清不止是最高统治者远不能及,就是由慈禧、光绪和慈禧的重臣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瞿鸿机等组成的领导决策集团中的重臣亦同样难称人意。据曾在清廷任职的梁士诒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的评价:
太后锐意维新,主媚外以安天下,惟所任非人,习于所安,(太后)对于守旧泄沓诸臣,意存瞻询,不肯决意淘汰。皇上则韬光养晦,遇事不发一言。荣(禄)有足疾,于政治上无所可否,皆迎合(西太)后意。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鹿(传霖)多执拗,瞿(鸿机)好挑剔。……此近日四军机之大略也。要之。近日非不锐意维新,而内外诸臣有血性者甚少。每一下诏,多粉饰敷衍,一奏塞责o
有论者认为这一评价有偏颇之处。例如,荣禄在促成慈禧同意变法方面实际起了重要作用。[2]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领导集团的成员大多有生理、心理或这样、那样的毛病。无疑这些年老力衰的军机大臣具有在传统体制下生存的足够的政治(权术)经验,但缺乏日本大化改新集团那种献身于变法的热情、理想和政治凝聚力,甚至必要的体力。然而,更不幸的是,随着1908年光绪和西太后先后逝去,借三岁皇帝溥仪之名,行保守、狭隘之政的摄政王载沣集团,在政治领导能力和应对时局变化的策略上,还不及慈禧集团,卒使变法修律益加艰难。分别在慈禧和载沣集团下忍辱负重地苦撑局面,从而使变法修律能有所成效的当首推沈家本和伍廷芳。他俩是晚清法律修订馆的主持人,虽被称为修律大臣,但与古代日本负责引进唐律制定日本律令的官员比,局限非常明显。日本的唐律移植者是在开明、能干的天皇和皇室领导下进行的,而且像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僧曼、吉备真备、大和长冈等,他们本身就是领导集团的核心成员;而沈家本、伍廷芳虽然主持修律,但不在新政的领导集团内,因此大政方针只能听命于他人。晚清处于领导位置的决策者虽然掌握了决定权和资源,但缺乏沈家本、伍廷芳那样的热情、视野和专业知识。久而久之,作为主持人的沈家本、伍廷芳亦不免心灰意冷。伍廷芳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著者初使美洲,见外域政治修明,富强鼎盛,视中国之萎靡不振,判若天渊,由是维新变法之心怦然而动。归国后,叠官农、商、外务,力主变法图强,娓娓指陈,具有条理,使当日上下一心,倾城相与,何至事事失败,见挫强邻,民心乖离,酿成党祸,令朝纲隳于一旦耶?回忆其时,劝导改良,几于唇焦舌敝,奈言之谆谆,听者藐藐,或唯唯称善,然总以难期办到为辞。久之此心废然,渐灰热念
比较之下,日本的唐代法律文化移植者不只是拥有权力,而且还拥有当时东亚最先进的文化和专业知识。前所说明,高向玄理、僧曼、吉备真备和大和长冈都是日本派到中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学习生活几十年,对中国文化和唐代法律相当熟稔,所以他们亲自参与输入唐律制成本国法律,可谓是专家移植。沈家本进士出身,精通传统中国法律学术,对西方法律文化亦有相当了解,但还说不上精通。伍廷芳自费留学英国,入伦敦法律学院攻读法律,获英国律师资格,后出使美国,具备西方法律文化的知识和素养,但就其经历和学业看,他的法律专长还是偏重于英美普通法,对欧洲大陆法律文化难称洞悉。他和沈家本一样,都没有留学日本专攻欧陆法的经历,这使他们在移植日本化的欧陆法律文化方面受到制约。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中国政府不得不聘请日本法律专家,变法修律中重要的法律草案,除民事法中的婚姻家庭部分外,其他莫不出自日本人之手,这已充分说明了问题。
摘自:张中秋著《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比较研究:以唐与清末中日文化的输出与输入为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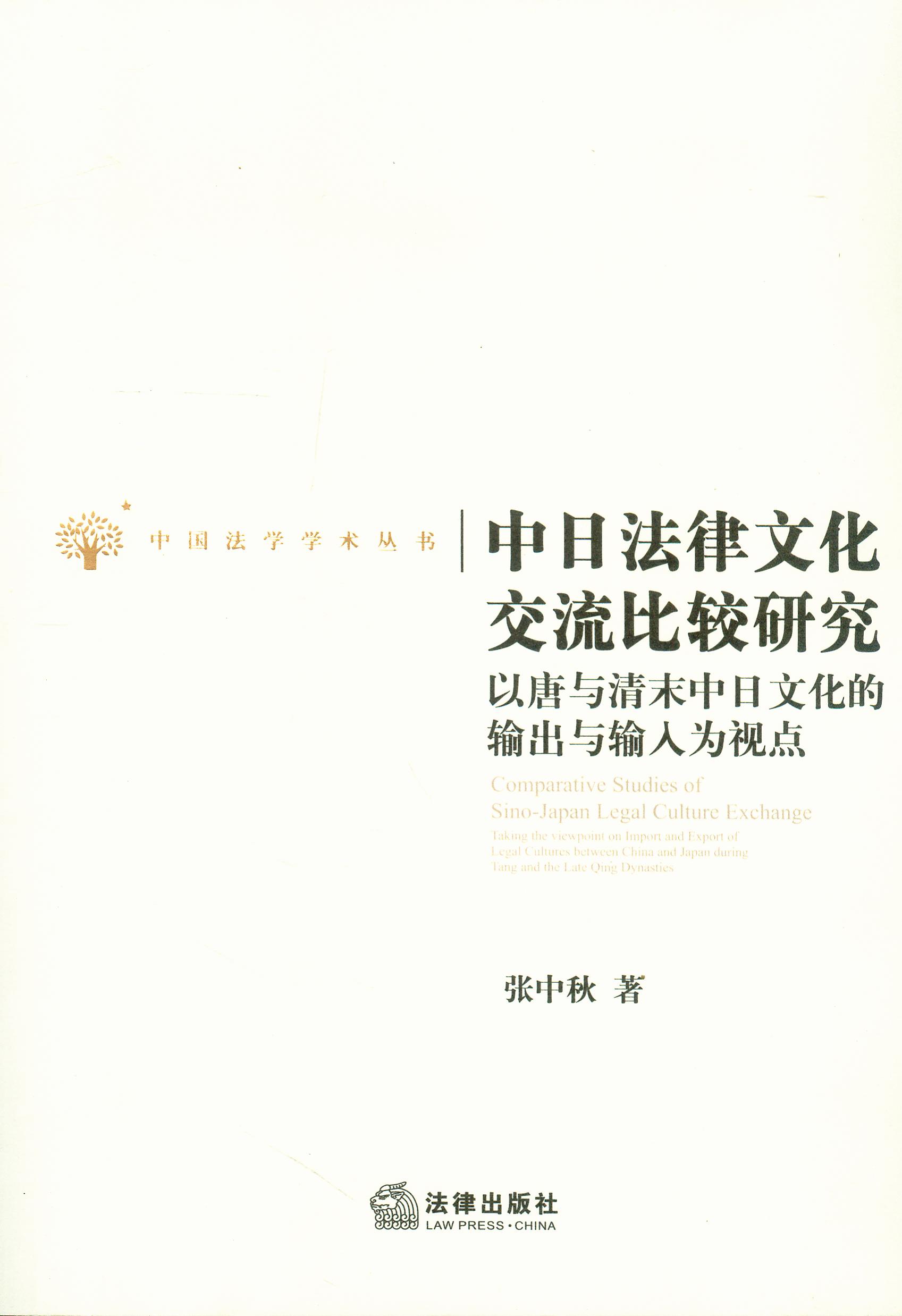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成败得失的人物观
中日法律文化交流成败得失的人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