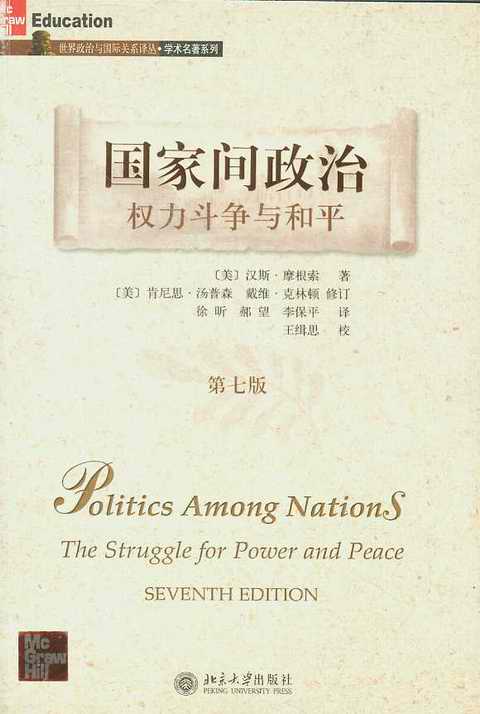
第四章
寻求权力的斗争:现状政策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不过是权力斗争这一现象的两种不同表现。权力斗争之所以在这两个不同领域中表现不同,是因为在各自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政治和社会条件各不相同。在西方,各国社会内部显示出比各国相互间大得多的社会凝聚力。文化的一致、技术的统一、外部的压力,尤其是政治等级结构等因素的结合,就使一国社会成为有别于他国社会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其结果是,国内政治秩序就比际秩序,比如说,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且较少经受剧烈的变动。
全部历史表明,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国家,或是在不断地准备战争,或是在积极地卷入战争,或是处于从战争中恢复的过程中。而战争就是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中,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作为一种大规模政治行动的工具的情形已变得绝无仅有了。但作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它在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中却依然存在;并且,对以革命形式出现的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恐惧,不时对政治思想和6为产生重要影响。①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在这方面的差异只是程度上的不0司,而不是性质上的差别。
全部政治,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揭示出三种基本的模式;也就是说,所有政治现象都可以简约为三种基本类型之一。一项政治政策所寻求的,或是保持权力,或是增加权力,或是显示权力。
对这三种类型的政治模式,有三种类型的国际政策与之对应。如果韩国的外交政策趋向于保持权力而不是朝着利己的方向改变权力分配,捌该国奉行的就是现状政策;如果一国的外交政策目的在于通过改变现存的权力关系获得比它实际拥有的权力更多的权力一一换言之,其外交政策寻求的是在权力地位上的有利变化,那该国奉行的就是帝国主义政5c策;如果一国的外交政策寻求的是为维护或增加权力而显示它所拥有的权力,则该国奉行的就是威望政策。②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概括仍嫌粗糙,有待于进一步的细化完善。现状”(。tatus quo)这一概念源于“战前状况”这个外交术语,意指和平条约中常见的一项条款,这项条款规定敌军撤出占领区,将该领土归还给战前的主权者。例如,与意大利④和保加利亚。订立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规定:“同盟国的所有武装部队将尽速撤出”意大利或保加利亚领土,“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迟于自本条约生效起的第九十天”。这表明,在这一期限内,战前状况将在该领土上重新建立。⑥
现状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历史上某一特定时刻所存在的权力分配。人们可以说,现状政策在国际政治中所履行的功能,与保守政策在国内事务中所发挥的功用是相同的。作为现状政策参照点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往往是一场战争的结束;在战争结束之时,权力分配便被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在和平条约之中了。这是因为和平条约的主要目的在于用法津条文把前一次战争中的胜利和失败所造成的权力变动固定下来,并通过法律规定保证新的权力分配的稳定性。由此看来,现状政策的典型作]用似乎是维护终结上一场全面战争的和平解决方案。从1815年到]1848年,奉行现状政策的欧洲各国政府和政党在维护结束拿破仑战争÷的1815年和平解决方案方面正是这样做的。这些政府在1815年缔结神圣同盟的主要目的,即是维持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存在的现状。结果,神圣同盟主要扮演了和平条约即1815年《巴黎条约》的保证者的角色。
在这方面,维护1815年现状的政策与《巴黎条约》及神圣同盟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维护1918年现状的政策与1919年和约及国际联盟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存在的权力分配状况,在1919年的和平条约中得到了法律上的表述。而国际联盟的主要目标就是要维1919年和平条约所规定的1918年现状,借以维护和平。《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责成其会员国“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略”,这就确认了国联的目的之一是维持1919年和平条约所确立的领土现状。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间里,维护和反对现状的斗争,主要就表现为捍卫还是反对《凡尔赛条约》的领土条款以及《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关于这些领土条款的保证的斗争。因此,那些反对1919年所确立的现状的主要国家一一日本于1932年、德国于1933年、意大利于1937年一一断绝其各自与国际联盟的关系,从它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现状政策不只是表现在和平条约和支持和平条约的国际组织中,那些渴望维护某种权力分配的国家还可以把一些专门条约作为它们的工具。1922年2月6曰在华盛顿签署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①和1925年10月16曰在洛迦诺签署的《德比法英意相互保证条约》⑥就是这样的事例。
《九国公约》把美国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转变成了一项多边政策,那些在对华贸易方面兴趣颇大的国家,都保证要拥护这一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稳定当时存在于缔约各国之间的权力分配状况。这意味着某些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如满洲和许多港口所取得的特权,不仅应当维持不变,而且中国不应向任何缔约国让与新的特权。
《洛迦诺相互保证条约》力求以一项针对德国西部边界的特别条约,来补充《国际联盟盟约》第十条对]918年领土现状所作的一般保证。该条约第一条明确规定了对“德国和比利时之间、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边界领土维持现状”的保证。
特别应予指出的是,同盟条约往往在某些方面具有维持现状的作用。例如,在1871年反法战争胜利结束、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俾斯麦试图依靠旨在防止法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同盟末保护德国在欧洲刚刚赢得的支配地位。1879年,德国和奥地利结成共同防范俄国的同盟;1894年,法国和俄国缔结反对德奥联合的防御联盟。一个同盟担心另一个同盟在声称要维护现状的同时却致力于改变现状,由此引起的相互恐惧,是燃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战火的主要因素之一.
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缔结旨在维持现状的同盟条约,主要是鉴于德国可能改变现状的企图。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类似条约以及捷苏条约都具有同一目的。这些同盟在经受1935一1939年考验时所表现出的无效,是造成德国1939年进攻波兰的原因之一。1939年4月5日英国与波兰结盟是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次努力,目的是至少维持德国东部边界的领土现状。今天,苏联与东欧国家所缔结的同盟、西欧国家之间及其与美国所缔结的同盟,也以相似的维持现状为目的,这种现状是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权力分配在欧洲的这些相应地区确立的。
有一项现状政策对美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并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基石,它的表现就是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是门罗总统于1823年12月2日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所作的一个单方面声明,它规定了任何现状政策都具备的两条根本原则。一方面,它保证美国将尊重西半球的权力分配现状:“我们没有干涉过任何欧洲列强的现存殖民地和保护国,将来也不会干涉。”另一方面,它声明美国将抵抗任何非美洲国家对西半球权*力分配现状的任何改变:“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宣布独立并保持着独立的政府,……任何欧洲列强为了压迫它们或以任何方式控制它们的命运而进行的任何干涉,我们都只能认为是对合众国的不友好态度的表现。”正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1933年4月12日在泛美联盟理事会上所s3作的讲演中表达的那样:“它[门罗主义]的目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反对任何非美洲国家以任何方式获得对本半球其他领土的控制权。”⑨
我们已经指出,现状政策是以维持某一特定历史时刻存在的权力分配为目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现状政策必然反对任何变化。它并不反对变化本身,而只是反对任何会导致两个或更多国家间权力关系发生逆转的变化一一比如说,A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强国,而B则升至A先前占据的显赫地位。而权力分配的小幅调整则由于保持了有关国家相应权力地位的完整,所以是完全符合现状政策的。例如,美国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这块土地当时并没有影响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现状,因为从当时的交通通讯技术和战争技术来看,美国获得这块当时无法进入的土地没有对美俄之间的权力分配产生任何可感受得到的影响。 0
与此相似的是,美国虽然于1917年从丹麦手中获取了维尔京群岛,!但它并未采取一项旨在改变涉及到中美洲各共和国现状的政策。虽然]就保卫通向巴拿马运河的航道而言,获取维尔京群岛大大改善了美国的 ]战略地位,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和中美洲各共和国相应的权力地位。获 ]取维尔京群岛也许加强了美国在加勒比地区既有的支配地位,但并没有 ;创造这种支配地位,因而它与现状政策是一致的。人们甚至可以说,通过加强美国在中美洲各共和国的优势地位,实际上巩固了权力分配现状,从而也就满足了现状政策的目标。
1962年初,苏联为了大大扩展它的影响,着手在古巴部署导弹。肯尼迪政府衡量了迫使苏联撤走导弹的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包括空袭在内,最后,它选定了封锁和隔离的政策。作为肯尼迪一赫鲁晓夫协议的结果,苏联人撤走了他们的导弹。但苏联继续以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支持卡斯特罗政权。与此同时,古巴则寻求它自己在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的意识形态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格林纳达和尼加拉瓜这类国家里发现了古巴和苏联的军事援助和军事人员。姑且不论这些国家中的民众是否支持古巴的干涉,美国决策者所面对的问题是现状受到威胁的程度如何。古巴独自的干涉威胁了现状吗?古巴作为苏联代理人的行动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吗?苏联的卷人是否破坏了门罗主义和肯尼迪一赫鲁晓夫协议,其卷入本身是否威胁了现状?从约翰.肯尼迪开始的历任政府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1983年10月25曰,里根政府入侵了格林纳达,表面上是要保护该岛上的大约一千名美国人的生命,实际原因却是美国人认为格林纳达是古巴人和苏联顾问在那里和加勒比其他地区策划军事行动的大本营。观察家们仍然会问,古巴和苏联的活动是否曾对该地区的现状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当里根总统的政策受到严厉批评时,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一些相互冲突的答案。判断苏古的卷入和美国决策者所作出的反应的标准是,权力分配以及现状是否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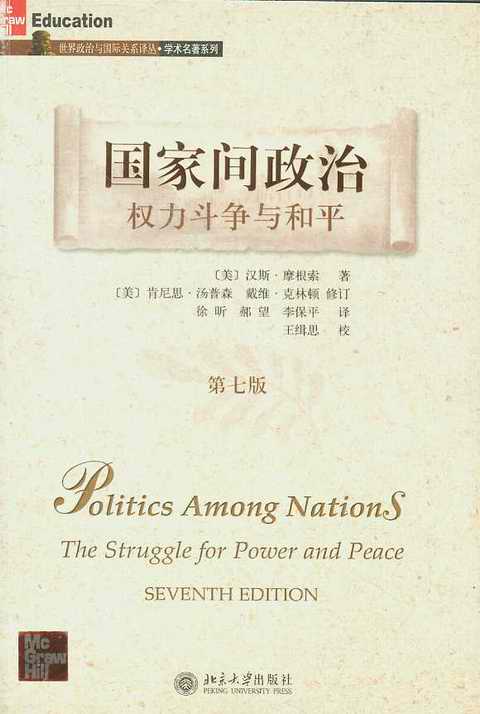 第四章
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