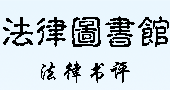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法律科学文库)》书评 ——
张维迎 2003-6-9 9:42:24
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评《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张维迎
1999年8月30日,沈阳市颁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的主要精神可以概括为:在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时,如果机动车方无违章行为,行人负全部责任。从侵权法的角度看,沈阳市的新办法意味着责任赔偿规则的一个重要变化。长期以来,大部分地区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时实行的是“严格责任规则”(strict liability)(或者说是“无过失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机动车辆对行人造成伤害,无论机动车方是否有违章行为,都得承担赔偿责任(当然,赔偿的具体额度依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新办法用“过失责任”(negligence rule)代替了严格责任,也就是说,按照新办法,仅当机动车方有违章(过失)行为时,才承担赔偿责任。
沈阳市新办法很快被一些其他城市效仿,同时在多家媒体上引发了一场所谓“撞了白撞”的大讨论。在众多的讨论文章中,所持立场反对者居多。反对人士除了一些普通公众外,也有法学界专家。如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在《人民法院报》上发表文章认为,沈阳市的新办法是反人道的、反正义的、反人权的;他进一步认为,在交通事故处理上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即机动车方的严格责任)。
这场大讨论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具体的法律(或法规)是否合理?在我看来,对沈阳市的新办法的批评大多是基于把法律看做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有人可能愿意认为是从“公平”的角度判断法律的合理性。按照这个标准,因为平均而言,行人是“穷人”,是“弱者”,司机是“富人”,是“强者”,所以,无论司机有无过失,让其承担责任是合理的。
但是,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也就是说,如何使整个社会的蛋糕变大(或使社会成本最小)。衡量一个法律是否合理的首要标准应该是效率标准,而不是分配标准。当然,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法律都无须顾及分配问题。我的意思是说,分配原则应该在效率原则之下,如果离开了效率标准,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比如说,如果只从分配标准出发,穷人盗窃富人的资产就不应该构成犯罪行为,弱者伤害强者也不应该构成侵权行为。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不会有人有积极性工作,不会有人有积极性积累财富,整个社会不会有进步,所有人都会在相互掠夺的过程中死去。相反,依效率标准,任何盗窃行为都构成犯罪,任何伤害行为都构成侵权,生产,而不是再分配,是每个人致富的最有效手段,整个社会就会不断进步。
分配标准是事后(expost)标准,效率标准是事前(exante)标准。尽管法律的执行在事后,但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事前,也就是说,法律的首要目的是通过提供一种激励机制,诱导当事人事前采取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动。当事前的效率(exante efficiency)与事后的效率(expost efficiency)发生冲突时,事后标准应该服从事前标准。这一点可以用“杀人偿命”的规则来说明。设想A杀害了B,我们应该如何处治A呢?从事后的角度讲,给定B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再让A以命抵命是没有效率的,为什么要死两个人呢?比如说,最优的办法可能是把A送到新疆种棉花,让他继续为社会创造剩余价值,而不是把他枪毙。但这样做的后果是,由于处罚对杀人犯没有足够的威慑,会诱使更多的人事前选择杀人,从而死的就不只是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杀人偿命”是合理的,因为它提供了最有效的事前防范激励(为什么在有死刑的国家凶杀案仍不断发生?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死刑并不构成对凶杀行为的足够惩罚,但这是现代社会所能实施的最大惩罚。可以设想,如果有比死刑更让潜在凶手畏惧的惩罚,用这种惩罚替代死刑可能是更优的选择。但常言道“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意味着死是最让人恐惧的惩罚了。另一个原因是杀人凶手被发现和判决的概率太低。如果潜在凶手预期有百分之百的概率被判死刑,凶杀大概就不会发生了)。进一步,即使B的家属愿意与A通过谈判私了(对双方而言,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最优),或者愿意“以德报怨”原谅A,法律也不能允许,因为杀人行为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对受害者家属的私人成本,受害者家属愿意接受的货币补偿不足以阻止从社会角度看不当的犯罪行为。当然,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受害人想实施的惩罚可能远远大于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惩罚,所以法律也不能允许“私了”。事实上,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差异是划分民法管辖范围与刑法管辖范围的一个主要标准。一般来说,二者差异越大,就越应该属于刑法管辖。因为即使同样的行为,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不相同,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也可能不同,所以刑法和民法的最优管辖范围不仅在不同的国家不同,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也不同。把法律看做是一种激励机制,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点。
回到交通事故的情况,当交通事故发生在行人与机动车辆之间时,受到伤害的通常是行人,也就是说,机动车司机是“施害者”,行人是“受害者”(所以人们说“车把人撞了”,而不说“人把车撞了”)。从事后的角度看,既然事故已经发生,行人受到了伤害,无论司机有无过错,让司机赔偿行人似乎是合理的。但从事前激励的角度看,可能不是这样。一般来说,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和事故带来的损害程度是由机动车方的行为和行人的行为共同决定的。法律的目的是为行人和司机提供一个激励机制,使得双方都采取最优的预防,从而使得事故的期望损害(等于事故的概率乘以事故带来的损害)加预防成本的总和最小。我们可以比较几种不同的赔偿规则对司机和行人的激励。为此,让我们假定交通规则本身是社会最优的,也就是说,在双方都严格遵守该规则的情况下,事故发生的概率处于社会最优水平(注意,不等于事故发生的概率最小,因为最小概率可以在不允许机动车上路的情况下达到,但这不是社会最优的)。第一种规则是“无责任规则”(no liability):在任何情况下,司机都不承担赔偿责任。此时,因为事故的所有损害都由行人承担,司机没有任何积极性预防事故的发生;相反,行人有最大的积极性预防事故的发生。与社会最优的预防相比,司机的激励不足(不遵守交通规章),而行人的激励过度(如绿灯亮时也不敢过马路),所以是没有效率的。第二种规则是“无过失责任”(司机方面的严格责任):在任何情况下,司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此时,司机有最大的积极性预防事故的发生,而行人则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谨慎行走(因为有些人身损害不可能被完全补偿,行人不可能不承担任何损失,所以,行人会选择最小的谨慎)。与社会最优相比,司机开车过于谨慎(也只能如此),而行人走路过于莽撞(如乱穿马路),因而也是没有效率的。第三个规则是“过失责任”:如果行人违章而司机没有违章,司机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司机违章而行人没有违章,司机承担全部责任(我们这里不考虑在双方都违章或都没有违章情况下的事故责任赔偿问题)。此时,司机和行人都有积极性遵守交通规则,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达到最优。这样看来,沈阳市的新办法用“过失责任”代替长期习惯形成的“严格责任”,看似无情,实则有情,因为它可以减少不幸事故的发生。当然,这里的一个假设前提是交通规则本身是最优的。如果交通规则本身不是最优的,遵守交通规则就可能是没有效率的。但此时要修改的是交通规则本身,而不是用“严格责任”代替“过失责任”。
前面,我假定司机的预防成本和事故损失都只是当事人的私人成本,赔偿规则只是在司机与行人之间分配责任。事实上,至少在大城市,司机的预防行为和交通事故导致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私人成本。如果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得放慢速度,交通堵塞就会加剧;每次事故发生,会使交通中断一段时间。交通堵塞和中断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考虑到这一点,尽管“过失责任”比“严格责任”更有效,但由于当事人(无论司机还是行人)仍然不需要补偿自己的违章行为对社会其他成员由于交通堵塞带来的损害,他们的预防激励远远不够。所以,我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交通事故中的违章方除了赔偿直接受害方的损失外,还应该适当赔偿由此导致的交通堵塞带来的间接的社会成本。
自科斯教授于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的著名论文以来,法律经济学在西方学术界已成为最热门的研究领域(据有人统计,科斯的论文是法学刊物中被引证最多的论文),吸引了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该领域的许多研究成果对推动西方法律制度(包括法律条文和法院的判决)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国内,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刚刚起步。王成博士《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是国内作者出版的少数法律经济学专著之一(如果不是第一本的话)。作者从激励的角度对侵权损害赔偿作了全面分析。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理论分析贯穿在大量的实际案例(特别是中国的案例)分析中。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不仅对推动中国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变革(特别是民法典的起草)产生积极的影响。我希望,我的这个序言有助于读者对本书内容的理解。
2002年2月于北京大学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