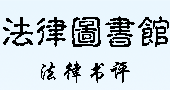刑事和解,着手“解”着眼“和”《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姜小东 2009-1-10 19:05:42
刑事和解,着手“解”着眼“和”姜小东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老子
读完《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一书,厌倦沉思,深有所感:有同感也有异议。刑事和解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大环境下唱响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社会机体多年积累,病体繁重。只用刑事的手术刀一阵猛割(例如严打),暂时起效的后果是犯罪的超量恢复。医治社会需要中医式的整体调理,手段要求温和。刑事和解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尤其自己的作用和方式。笔者认为,刑事和解要着手“解”,因为法律是解决问题的;着眼“和”因为解的目的是和,和才能更好的解。
中国几千领跑世界,社会治理制度保证了经济文化的繁荣,我们有自己的“法治”是一种各个调整方式的合治,并被整个亚洲文化圈国家不同程度的援引。清朝末年我国门被火炮打开,美梦被火车惊醒,开始或被动或自觉的放眼西方。一方面来看,国人丧失了天朝上国的自信学习西方;另一方面,现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必然趋势,社会的工业化必然要求与之适应的法制化。也就是说中国改革社会实现法治化是必然趋势,无论被入侵与否。本来是早晚的事,入侵就使此事办成了早的事,在中国没有准备好社会条件的情况下破门而入了。就想一个酣睡的人被突然的打醒,在不了解情况,还没有适应就投入了盲目追赶西方长跑中。致使制度缺乏设计,法律缺乏“汉化”,客观的讲确实没有时间考察,也没有相关法治技术。
时至今日,反观中国法治的三十年道路,与其说是法治史不如说是立法史。立法有绝对的量的优势,比任何一个西方发达法治国家法律在条数上应该说差距不大,法早已跳上了农民的炕头。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似乎法越多矛盾越多,在加强立法,矛盾比以前再多,进入了一种类似抗生素与病菌的变异对抗之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么,为什么唐朝的权力法制止到了县而社会良好,而今天的法侵入到每一个人却效果不佳?如同费孝通先生多年前所言:法制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发生了。
今日的中国,各种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构建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恰恰在于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与我们的固有的传统的文化价值相悖。我们并不是渐渐的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所以,以前的盲目移植,造成今天很多法律本身的弊端的凸显,有很多各方人士开始思考,这个社会是否需要如此的需要法律?
笔者认为,吸收一切的先进合理制度为我所用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但一定要与中国现实和传统相适应,最好是实现“法治的本土资源化”,法律最终是回应现实的。
在此,笔者打一个比太恰当的比方:中国当今社会错综复杂,如一头拾垃圾者的头发:长,脏,乱,差。
历史遗留问题:长,脏
转型中的问题:乱,差
这么一头长脏乱差的头发,交叉错综,纠结缠绕。而今天,我们经济发展了,有钱了,有地位了。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和外出国门见外国客人的需要,梳理是理所应该的。有基本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积弊已久,应先清洗数遍,慢梳清理,以求无伤身体,无伤头发。
今天,一些人甚至是专业的理发师,突然拿来一把钢齿锋利,排列整齐,原装进口梳子(移植法律),甚至只为了跟外国人玩的需要,不顾及健康和外观是否合适,非要进行发型设计,烫,染,拉,吹,弄成和洋人一样,黑的染黄,直的烫弯,玩的拉直。谈何容易?怎么可能?怎么可以?
是为了自己身体好,还是个人美观,是外国人看了又审美认同,还是只为了和外国人打扮的一样?是否只有这样他们才愿意和我们玩,还是我们才敢于和他们玩?我不知道原因,但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到结果:毛将焉附?毛将焉在?皮将焉附?头将焉在?“国将不国了”。
在法治约等于立法的观念支配下,立法庞杂扩张,司法力不从心,执法寸步难行。问题出在哪?很多“法律人”得出的原因是法制不健全,应加强立法,不断的开拓范围,细化操作。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式的法治是中国社会的 “理想图景”。于是法制被人类从诸多社会治理方式中遴选出来,赋予强有力的铠甲,向社会矛盾最激烈处用兵。法治的格外壮大已经快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而其功用与其规模并没有呈现出让人满意的比例。法治的机器,不断拓展社会空间,在不同层次深度,肆意蚕食鲸吞其他调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传统,伦理等温和性方式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当然,这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熟人社会但陌生人社会过程中必然损失的部分。但是由于法治机械化的硬性驱逐,引来了温性方式的反抗,这就是现在社会很多矛盾的病灶,更是西方式法治的水土不服。
其实很显然,“徒法不足以自行”。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应该说是最上层最坚硬的部分,必须依赖经济基础并与其他方式相互协调配合,才可能发挥最大良性作用。我国存在的问题在于错误的认为,引进了法治就当然的引进了法治社会,就只用法当然而治,不管不顾其它方式,进而替代排斥,甚至故意打压恶性侵入。这样的后果是法条数量上有绝对优势,制度范围铺满社会各个方面,造成法治的虚假繁荣。实际上,只顾为法治而法制,稍加整容的照搬西方模式,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结果在司法和执行中又被难以逃避的“秋后算账”。
法制冗沉,运作矛盾层层的当代中国社会需要刑事和解,刑事和解要“解”更要 “和”。和谐社会是我们今天的选择,是解决中国社会前进中问题的希望,我们要 “和”。但是法律是要解决问题的,尤其是刚性的刑事法律,向来不是标榜 “和”,而是注重 “解”即解决不可调和的问题,用权力说理,这也是刑事法的功用。
笔者认为,一国之法应该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民族心理等相适应相谐调,才可以发挥人类预期的最大功效。唐朝虽然权力只到县级,但是县以下交给了乡绅阶层和伦理习惯,这是有唐朝的社会结构决定的,法制代表国家权力的自上而下贯彻,伦理习惯代表社会的自下而上自治,二者合并完成了控制社会体系。近日的中国社会,就像一个配置较低但高速运转的电脑系统。产生了的问题只靠法治这个杀毒软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优化大师”的优化,因此和谐社会的提出和贯彻是正当而及时的。和谐社会应该合理消化发展中的矛盾,运动中的磨损,很多问题不需要进入司法领域就可以解决。也就是要转变观念,放弃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权利贯穿渗透,重新考虑定位社会的自洁能力,发挥其他调整方式的第一屏障作用,法治屏障后放。这样不但节约社会治理成本,节省法治资源,减小社会创伤,而且可以使法治进入良性发展道路。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刑事和解显得尤为重要了。面对社会急剧发展转型的时空,各种矛盾突出涌现,杂错交织。正所谓“毒草百步,必有解药”,要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必须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内部着手。就像青霉素的发现是从葡萄球菌培养皿的“菌团”中产生的。实际上,我国已经有过十分类似的范例: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面对当时的大环境难以生存,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农民按下手印的不长时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小岗村从而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这就经历了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既要积极改善不理想的大环境,又要静观其变善于发现,对于毒草丛生的大地整体着眼,从总发现解毒草,提取加强并推广是一个十分合理的方法。而不应该主观闭门造车,或者盲目照抄引进做毛泽东批评的“留声机”。
如果试图演绎上述过程,那么在毒草遍地矛盾交错的大环境中又没有解药?是否发现了?是否可以提取推广?答案是肯定的。解毒草中比较典型的一株就是“枫桥经验”。所谓“枫桥经验” 是指1963年,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为此,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从现实看,“枫桥经验”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
“枫桥经验”是毛泽东同志批示的、我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四十年来,当地人民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内涵: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实现农村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枫桥经验”也因此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党政领导,各负其职,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枫桥经验”对于进一步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学习运用“枫桥经验”的意义已经论证,怎样学习、灵活运用“枫桥经验”或者有没有“柳桥经验”这是进一步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牵涉到运作的配套制度设计,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还需要多论证多实践。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