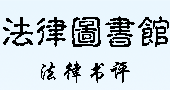读汉译《古代法》札记之一:《古代法(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邢克光 2007-2-2 19:06:58
读汉译《古代法》札记之一:简单的评述 邢克光撰
1861年,英国法学家梅因(Maine, Henry James Sumner, 1822-1888)发表了一本题为《古代法—它与早期社会历史的联系和现代思想观念的关系》(ANCIENT LAW---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的专论。这本书在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1959年,又根据原文另行移译出版,并列为该馆编辑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我所看到的是1996年7月该版第5次印刷本,译者沈景一。
这是一本研究法理学历史的经典著作。它的特色是从法律的角度考察了古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又从历史的观点研究法律的发展及其动力;澄清了在法律和历史两个方面许多比较流行的、但又十分模糊的思想观念。书中有大量的警句箴言,表达了作者独到的见解。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我认为这句格言对任何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这种研究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探究某一项法律制度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对当今社会的影响程度;二是与其它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做客观的比较;从而在纵横两个方面考察并鉴别其异同和得失。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梅因的这本书给我们在法学研究上做出了榜样。
梅因认为法学理论来源于成文法典或不成文习惯法的说法都与事实不尽相符,但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后果。实际上,早在有法典之前,人类社会就存在许多“法律现象”(legal phenomena)了。许多古代文献记录就提出了法律概念的早期形式,例如荷马诗篇中的神话和英雄故事,就有议事集会、法律和司法、审判等名词。在“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阿基里斯的盾牌上面,有“火及工匠(或冶炼)之神赫菲斯脱斯”镂刻的一幅“诉讼和审判”浮雕画。荷马把画中的“审判”情节描写得栩栩如生,恐怕并非完全出自于想象(参阅本文所附的“校注选”之四)。
梅因把远古时代的法律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英雄时代”原始君主的“ 神授”法律,“贵族时代”的不成文习惯法和以后的法律法典化。
历史中的“英雄时代”,依靠个人出众的体力和勇敢而取得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他作为原始君主,还要靠智慧,去维护其统治,法律便是重要的统治手段之一,被认为是“神的意志”授与君主掌握。他运用“神道设教”,成为宗教的首领或最高祭司。典型的例子如古雅典负责祭祀的“大执政”(King archon),古罗马的皇帝兼“至尊祭司”(Rex Sacrificus)。这很像我国古代帝王,尊称“天子”,同时也是祭祀的主祭人。即使在世袭的王权被削弱,并把统治权让给贵族集团的时候,君主往往仍旧保留着神权。例如在我国春秋时期,周室式微,公卿执政,“诸侯不享觐。天子之在者,唯祭与号”(《谷梁传》昭公三十二年)。他们虽然还保留着天子或者周王的称号,但是已经没有王权了。其他各个封建国的诸侯,也大抵如此。
“贵族时代”是一个不成文的习惯法时代。贵族集团垄断着法律知识,极大多数人只知道有“王法”,但不知道有哪些法律,不同的法律之间又有哪些差别。我国古代也有过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把法律铸成“刑书”,公之于众,就曾遭到晋国大夫叔向的指责,他说,这么一来,法律公开了,让老百姓都知道了,以后事无巨细,都去求法律解决,不但争端从此增加,而我们这些掌权者(即贵族们)也就不能随意地统治下去了(《左传》昭公六年)。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二十多年之后,晋国的范宣子和赵简子,也先后“著刑书”、“铸刑鼎”。这时,没落贵族孔丘再也忍不住了,批评他们不守晋国的旧法度,把法律公开了,“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这里,“何以尊贵”是无可奈何的哀叹,“何业之守”倒是大实话,“何以为国”则是内心恐惧而发出的恐吓。怪不得这位夫子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对于贵族集团垄断法律,是颇为有用的主张。
从上述的古代文献记载,可以看出社会进步的思想潮流毕竟不可阻挡,随着贵族政治的结束,也同时开始了法律的法典化时代。这里所称的“法典”,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而只是把当时存在的习惯法或惯例加以整理,使之条理化,用文字形式加以记述,以便在审理案件时具体引用;一般说,还没有专门的法律理论,似乎也不需要法律理论。正如我国晋朝的杜预所说,“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晋书·杜预传》)。
梅因还指出,一个特定的社会在其原始状态下所采用的习惯或惯例,如果已经不适合继续促进物质上和道德上利益的需要,并且迷信它们应该永远存在而编入法典,那就会开始这样一个过程,那就是“从合理的惯例产生出不合理的惯例”。也就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走向反面。习惯和惯例在“法典化”之后,就再也没有法律性质的自发的发展了。以后推动法律与社会和谐一致的动力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衡平法”(Equity)和“立法”(legislation)。
“法律拟制”是指对原有法律在形式上或字面上保持不变,而实际上却以一种假设的或者隐蔽的手法改变了法律的规定。例如,古罗马的“法学家解答”(Responsa Prudentum)在声称《十二铜表法》等成文法有约束力的同时,却在变动或改变它们的规定。因为当时许多著名的法学家受到极度推崇,他们的意见几乎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具有同等的约束力。梅因认为,法律拟制在早期社会是绝对需要的原始手段。甚至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的法官还对议会通过的《限定继承法》(statute of Entailment)用普通法上的“共同取回之诉”(Action of Common Recovery)程序去规避该制定法的效力。通过这种虚拟的诉讼程序,形成一个先例规则或者一条不成文规定,那就是:“不能用明示的语言产生限定继承权” 。
“衡平法”是在原有的法律之外,建立一套不同原则的法律规则。“衡平”(equity)这个名词的基本含义既代表公平、合理、正义,又代表在特定情况下运用的法律。这两点不论在西方或者中国,都是一个很古老的概念。例如,我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对于“灋”(也就是今天的 “法”)这个字的解释,其主要含义就是“平如水,触不直者去”。罗马的衡平法(Æquitas)是万民法和自然法的混合物。一般认为是来源于希腊文的íσóτης,意思是“均分”。明确地带有“平准”的意思,平准的倾向是万民法的特点。早先纯粹的罗马“公民法”(Quiritarian law)对于各个阶级的人和各种财产古罗马的衡平法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处理外族人不能享有市民法上权利的问题,采用裁判官的“谕令和裁决”(Edictum et Decretum)等方式,这就是后来所称的“裁判官法” 。
而十三、四世纪开始出现的英格兰衡平法,则是建立在“公平审判”的道德原则基础上,处理因为没有“令状”(writ)而不能按普通法程序起诉的案件。从请求国王给予“法外施恩”开始,发展成为一套复杂的独立体系。而与此同时,衡平法在对案件的推理方法上,“遵循先例”的原则上,仍然跟普通法一样,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关于“立法” ,梅因认为是一个国家在青年时期要求直接排除某些社会弊端,以及为了调和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的矛盾,因而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通过立法加以明文规定,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这样,社会才能在大乱之后,开始平静下来。由于社会的需要和社会意见常常走在法律之前,所以应该是立法者考虑的出发点。不过要注意,在社会的幼年时期,法律过早成熟,往往会因实施困难而夭折或名存实亡;反之,法律过于陈旧僵化,也会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阻碍社会的进步。
梅因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研讨了罗马法上的家庭、婚姻、财产转让和继承,以及契约等等问题。
长期以来,古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或家族。“家法”要远多于“国法”。佯称具有同一血统的“收养关系”,目的就是要维持“家”的继续存在。这同我国古代保持同一血统关系的家庭或家族观念完全不同,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左传·僖公十年》);“非其族类,不歆其祀”(同书三十二年)。汉代经学家注解说,这是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我国古代承先启后的法典《唐律·户婚》据此规定:“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疏议》解释说:“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一年;违法与者得笞五十”。但也有例外。唐代的杜佑在其编篡的《通典》里写道:“若以异姓为后,可同于女子出适”( 卷六十,《礼》二十)。直到《大清律例》仍旧有规定:“其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户律》)。
罗马的家庭以“家父”的最高权威为代表。家父不仅是立法者 ,而且是审判者。未成年的子女和奴隶一样,被当成是物,可以出卖。到罗马帝制后期,家父对于家子的人身控制逐步放宽,而对其财产控制则反而更加严格。家子取得的财物,完全归家父享有;家父除了对家子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之外,不承担其他财产义务。这一点同我国古代法律规定十分相似。《唐律·户婚》中就有“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后来古罗马对于从军的家子“占有”的“战利品”(peculium castrense)和受奖赏的财物,才可以作为他自己的财产;更后来,对于担任国家公职的家子个人收入的财物,也给予法律保护。而在我国,一直施行到二十世纪初的《大清律例》,仍旧规定不许子孙“别籍异财”。
但是,“家父权”对于妇女的人身和财产格控制,则从来没有放松过。表现在对妇女的“终身监护制”上,我国古代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义”,在欧洲直到十九世纪,还继续存在,而罗马帝国早已灭亡一千几百年了。
古罗马的遗嘱继承观念和制度,和现在完全不同。首先,立遗嘱是公开进行的,因为那是一种转移财产的宣告或“诉讼”;其次,遗嘱和继承是同时完成的双方行为,不能更改或取消;所以遗嘱在立遗嘱人生前就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了。而现代的遗嘱则是秘密进行的,是立遗嘱人的单方行为,可以更改或取消,并且只在立遗嘱人去世之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在古罗马,一个人未立遗嘱而死去,将是莫大的耻辱,因为这意味着他的家系从此中断了。这同我国古代所称的“绝嗣”、“无后”而“断了香火”一样,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古代的财产制度是由原始社会的共产制或公有制到家族共有制,以后再发展到家庭(相当一个“单一法人”)所有制,而个人的财产则是最后才产生的。罗马法有关财产转移的手续十分繁琐,并且具有高度礼仪性,要有主持人,司秤和一帮证人在场,有许多象征性的行为和语言,不能有丝毫差错和缺失,否则转让无效。随着《十二铜表法》有关“时效”的规定普遍实施,裁判官发出保护“占有”的“禁令或强制令”(Interdict or Injunction)以及法律拟制的“串通诉讼”(actio collusum)等等,才使财产转移的严格形式主义得以宽松,并且最终完全消失。财产的广泛分类也随着逐步简化,最后只有土地和动产两类。现代法律把不动产定义为“土地及其定着物”,把动产定义为“一切非不动产”,这样极其简单而且明白无误的语言,是罗马法措词的特点。
梅因说:‘ 迄今为止,所有进步的社会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from status to contract)的运动 ’。恩格斯曾经对这一论断评价说,就这句话的正确性而言,他和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提出来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75页)。这就说明梅因即使是采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观点而提出自己的说法,也不失其为一种科学态度,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家。另外一个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在有没有“从契约到身份”这种新的反向运动呢?恐怕这也是现代契约法理论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关于契约的早期历史,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很难理解,以致错误地把现代社会的种种契约原则,契约上的权利和义务等等,搬移到古代社会,认为“古已有之”。梅因特别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极力反对,加以全盘否定。因为这种理论是从抽象的思维出发,不符合历史事实。真象是,在早期社会既没有个人与个人之间,也没有一切人同一切人之间的契约,而只有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之间的契约,并且是在极为隆重的仪式中订立的。契约只不过是一种神圣性的允诺,只要举行过仪式的允诺,就要履行诺言,哪怕这种诺言是在欺诈或者胁迫之下作出的。由此可见,订立契约的道德义务或道德原则,在古代并不存在。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道德的东西并非自始规定为与不道德的东西相对立”(《法哲学原理》第二篇第108节)。契约的道德原则是随着商业交易行为而逐渐产生的。《文心雕龙·书记第十七》里有这样一句话:“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书中进一步解释说:符的意思是信任、防伪;契的意思是记数、记事;券的意思是约束、“以备情伪”和“以坚信誓”;疏的意思是以“小券短书”表达最贴近的用意。在交易上,这些既是用做法律上契约义务的凭证,也是要求表示“诚信”的书面形式,即商业上道德义务的凭证。
通过上述对道德原则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梅因的道德观,它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服从和强制,更确切地说,是靠长久以来形成的本能和习惯,特别是商业习惯形成的惯例规则,而不是靠明文规定的强制或制裁手段。例如罗马法里继“正式契约”(contractu)之后出现的“简约”(pactum),不仅有利于交易的要求,而且也是道德进步的标志。再往后,由于法学的进步,大多数契约都归入了简约一类,道德义务的原则才算最终确定下来。
契约的早期名称是“耐克先”(nexum),意思是‘每笔交易都要用“铜权和天平”(per aes et libra)而结合在一起’。而这个定义恰恰又是买卖奴隶和转让财产的必要条件和程序。比照现代的法律观念,订立契约产生债权,让与财产则是物权的变更,两者之间界限分明,不容合二为一。
罗马法的契约分类,在其发展过程中依次有口头的、书面的、要物的和诺成的四种,至今仍旧是合同分类的基本形式。对于简约来说,还必须要有“对价”(consideration),即“以什么对什么”(quid pro quo)。这条规则,在实施英国普通法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仍旧普遍采用。而在实施“大陆法”的国家和地区,则采用“约因”(causa)这个概念,实际上两者之间虽有联系或共同之点,但却有严格区别。
关于侵权和犯罪行为,在罗马法里不是重点;两者在古代社会也很难区分。早期有关处罚的法律,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刑法”。现代人们所称的许多犯罪行为,在当时则完全按照侵权行为处理;在处罚方面也没有什么限制,并且允许以支付“赎(罪)金”来代替“血亲和同态报复”(vendetta and talion),这在古希伯来人的《圣经》和古代巴比仑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已有相当详细的明文规定了。
最早审判刑事案件的“法院”,只是立法机关的一个临时委员会,除了审理案件之外,还同时针对该案件通过相关的法律。根据这样的情况,可以看出罗马的“刑事法院”数量很多,定罪量刑反复无常,没有统一的标准。各个“法院”之间没有明确的管辖界限,相互之间也没有联系;但是,每个法院对于其他法院的有罪判决案件不再受理,而对无罪判决的案件则予以受理,这可能是唯一的共同点。随着这种临时委员会的裁并和改为常设的机构,才在最后形成了独立的“刑事法院”。另外,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之后,教会不仅逐步掌握许多世俗法律事务,如出生和死亡、婚姻和财产继承等登记,还根据《摩西戒律》所规定的宗教罪中,挑出一些作为对世俗审判权的管辖范围。例如把“异端”和“伪证”,划归宗教法庭,而把“谋杀”和“强盗”划给世俗法院。我们可以从卡尔文教派的“宗教裁判所”强加给“异端”的罪名,不仅是于法无据,无中生有,而且采用的逼供信手段和施加的酷刑,也是空前的;这就足以证明在“宗教改革”之后,欧洲还没有真正的刑法制度。
读完了《古代法》全书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梅因所论述的古代社会和法律,是以古罗马为主流,以古希腊、希伯来、印度和中世纪开始前后日耳曼各民族以及罗马教会等为支脉,或者说,主要限于雅利安民族的古代社会和法律。另外,他同时还把英吉利法同罗马法进行了对照比较,指出了两者之间存在的某些传承关系。他在本书序言中一开始就宣称他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罗马法。他对于当时英国学术界人士,对罗马法的极端无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狭隘心理和傲慢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反之,他自己则对罗马法推崇备至,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说:“罗马法,尤其是罗马的“契约法”,以各种思想方式、推理方法和一种专门用语贡献给各样的科学……除了“物理学”之外,没有一门科学没有经过罗马法的过滤 ……“政治学”、“道德哲学”甚至“神学”,不但在罗马法中找到表达思想的工具,并且以罗马法为其最深奥的研究所养育成长的“发源地”(原文是nidus,原意为孵卵的地方,译文为“卵巢”,误。) ……在西方,能够很精确地用来研究哲学的唯一语言是罗马法的语言,如果罗马法提供了语言上唯一正确的媒介,更重要的是,它同时提供了思想上唯一正确的、精密深邃的媒介”(这段全文参见汉译《古代法》第191页至192页)。这些话即使在今天,对我们就罗马法及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否应该有加以认识、探讨和参考的价值,或许是本书留下的话题之一。
最后,由于作者在全书中除了一则注明出处之外,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注释,这对于即使受过专门训练的读者,恐怕难免感到许多不便;更何况本书的汉译,虽说是重新“另行移译”,但“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见出版说明),极有可能沿用旧译的地方,存在许多历史事件、专业术语乃至一般词语的翻译错误。这些错误不能不说也是译者、编辑和读者应加注意的话题之一。这些话题,对于如何比较正确地理解和介绍外国学术文化、特别是法学历史文化,都是应该重视的。本文作者不揣浅陋,从大量翻译错误中选出几条加以校注,见笑于大方之家。□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