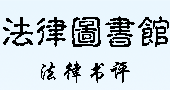走出“迷信”天地宽《法治与“民主迷信”》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金钊 2007-1-15 9:15:26
“自由民主的胜利与历史的终结,自由民主似乎成为我们时代的唯一选择。民主似乎成了一种宗教,一个神话。”——福山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由一个哲学上的立法者根据一定的原则来建立的,而是由人们多样而多变的需要经年累月不断进化而成的。它不是逻辑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
——古斯塔夫•勒庞
一、 导言
潘维先生无疑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在外有“世界民主第三波”大潮汹涌袭来,内有“中国政治改革就是民主化改革”的呼声呐喊助威的当代中国思想界,公然与民主化思潮唱反调,无疑是将自己摆在了一个靶子的位置,颇有“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悲壮色彩。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自从他发表了《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一文后后,对他的声讨之声便不绝于耳。其后来所著的《民主迷信与政体改革的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0年秋季号)、《民主与民主的神话》(《天涯》2001年第1期)等文章则更是将他本人坚持“法治主义”,反对“民主教”的观点“暴露无遗”。而摆在我面前的这本《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香港初版)可谓是他对近年来在上述问题上所作论述的一次系统性梳理,读过之后颇有些或同或异的感想,刍荛之言,未敢自是,姑录于此,以求教于方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就该书中与“民主”、“法治”有关的观点进行探讨,书中其他诸如“世界秩序”、“政治科学发展”等篇章不在此列)。
二、究竟有没有“迷信”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设定与路径选择上,“民主”总是作为最重要的选项出现的。不论是当初志得意满、胜券在握时的“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还是痛定思痛后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抑或是如今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民主历来都是每一代政治家的宠儿,即便是在那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年代,也仍有着与“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相匹配的民主话语,即所谓的“大民主”。
时至今日,不论是力图追求“政治正确”的政策性解说,还是对于未来中国政体的理想制度设计,抑或是对当下改革现实的理性解读,“民主”早已当之无愧地成为学者们谈论的头号“热门话题”,学术界呈现一片“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直到“民主迷信”说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才忽然意识到,原来所谓“百家争鸣”不过是“一呼百应”而已,更确切地说,其实只是一种声音——“民主是好的,我们应该追求民主”——的不同变调。因为当下各式各样的“民主诉求”或制度设计,尽管其在民主目标、实现方式上存在分歧,但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也即是,在二者的思考空间里,“要不要民主”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当然性前提。大多数学者都是在这个前提下展开论述的。而这些学者中又有很多人自称秉承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可他们恐怕忘记了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总是宣称自己是价值中立的,不预设任何善的观念。”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够沉下心来,回到研究的起点,对“民主”这一政治改革研究的这一核心逻辑前提进行清理,潘维先生这顶“民主迷信”的帽子并不过分。这也许就能解释尽管潘维对“民主迷信说”的论证并不充分(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论及),但却仍能刺痛很多人“神经”的原因了。而这种痛感在很大程度上则是源于历史深处的记忆。“民主”作为“舶来品”是被康梁等清末戊戌变法者从西方挪到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其后又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树起的“启蒙”与“救亡”的大旗之一。即使是在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时期以后,只要战事稍松,民主的呼声就还会冒出来,而且在专制独裁的打击下更加瞩目,使得当政者也不能不假民主之名行事。因此,推崇、追求民主,“为民主而斗争”既具有历史承接性,又具有价值正当性和“政治合法性” 。
然而,只要我们转换一下思考的角度,就不禁会为“民主”一词居然能在现实中与不同种类的非民主甚至反民主政体嫁接而感到吃惊。为什么民国初年曾为万民瞩目的“政党政治”的实践在经历的短暂的“喧嚣繁华”后最终惨淡收场?为什么力倡民主的一代伟人晚年会因“大民主”而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浩劫?为什么民主会被解读出如此不同的面貌?这一切难道仅用“历史局限性”就能圆满的解释吗?相信只要不是奉行“鸵鸟政策”的人都不会满意这样的回答,因此,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命题的“当然性”改成“或然性”,去掉百余年来其身上被涂抹的那些浓重的想象成分和感情色彩,透过表象去进行更深层的理性思考——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
由于民主这个词本身可以有不同层面的含义,比如它的理论规定、它的制度形态、它的价值意义等等。因此,民主究竟是什么?这样的提问实际上是大而无当的,因而其意义不大。所以,我们对民主的解读,必须联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政治文明进程所处的大背景来谈,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三、“取其精华”还是“拾人牙慧”: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悖论
在当代中国,民主化思潮甚或“民主迷信”的产生,其外部推动力无疑来自于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军事政变,无意中引发了一次世界性的政治运动,成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开端。在此后的整个20世纪晚期,大约有120多个国家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在发展速度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奇迹”:民主化在波兰用了十年,在匈牙利用了十个月,在东德用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十天,而在罗马尼亚则用了十小时。 这种状况使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惊呼,“突然间每个人都发现了民主!”他反问道,“今天的政治思想家,不论在什么意义上,有谁不是民主主义者呢?”
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确立是这次世界性民主化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成为这种民主改革运动的核心,而民主化进程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政府” 。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于短时间内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巨大胜利,其在范围和速度等方面创造的奇迹同西方民主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其先天的“不足之症”在“礼花”散尽后很快就显露了出来。
就已经过去的民主化进程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大多仅局限于宏观政治层面,主要体现为选举程序的普遍确立。因此,单纯就民主选举等制度建设来看,像土耳其、印度、斯里兰卡以及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的确可以称为民主国家。然而,现代民主制度的运行不但需要全体公民参与到政治选举与政治决策当中去,同时,它还需要有效地组织参与,以保证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这样,保证稳定的法治秩序就显得至关重要。就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来看,权力的争夺可能只是一夜之间的闹剧,但是,在那些刚刚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宪政体系的建立却绝非一日之功,民主权力与法治秩序的契合更需假以时日。正如美国学者拉里•戴尔蒙德所言,“在选举民主与自由民主之间的这种差距,已经成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差距将对理论、政策和比较分析产生严重后果。”
由此可见,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成了一场被“阉割”的民主化。一方面,公民通过民主制的建立取得了进入国家领域的政治权利;然而,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国家权力与公民社会之间界限还没有划清,法治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四、“结果”还是“起点”:大众民主、超级民主与宪政民主
在西方,原初意义上的民主源于古代希腊,雅典民主的精神“嫁接”了古罗马法治的因子,以“基因重组”的方式经过中世纪传给了现代西方。经历了长时间的“接力”与“组合”,西方社会才形成了宪政民主的“杂交优势”。即使这样,从民主制的确立到普选权的实现在英国甚至用了近两个世纪,美国也并不比英国短。
后来的经验表明,西方较为成功的政治文明成果——宪政民主——正是在克服这种“超级民主”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两相比照,我们发现,20世纪晚期实现民主的国家并没有形成“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相反,那些“速成”式的民主往往很难接受法治的约束,从而引起混乱与冲突。事实上,“宪政自由主义从理论上与民主不同,从历史上与民主有别”。 在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法治与民主这两条线索是相互交织的。然而当民主“洪传世界”时,西方学者却失望地看到,自由和民主在世界其它地方“分道扬镳”了。“民主繁荣了,宪政自由主义并未昌盛。”
恰如许章润先生所言,“一个弊病就是我们倾向于将人家历史上长期奋斗而来的结果——宪政架构和理念、一套民主政治的现成制度和做法,当做我们此刻的起点,希望据此起点而达致心中的结果。” 因此,将民主看成一个过程甚或是一种自觉的生活方式也许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但令人遗憾的是,有很多人面对民主地弊端和一连串悖论,却将其归罪于民主的缺乏。他们认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有更多的民主。”然而,“这样的方法无疑等于火上加油”,因为 “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 就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看,民主失败常常是因为民主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也就是所谓的 “民主政权的‘自杀’”。
五、“法治”在中国:命运多舛的“兄弟”
与民主相比,“法治”这个“同胞兄弟”就没那么讨人喜欢了。如果我们仔细地梳理这百余年来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始终是不均衡的:法治的发展要么是迫于革命的压力,成为应付革命的手段;要么是革命的成果,成为阶级力量对比的反映。可以说,法治建设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缺乏法治正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痼疾,深刻地影响了民主制度的有序发展。
从“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我们基本上不靠这些,主要靠决议、开会......” 到“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一生戎马倥偬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并没有选择法治之路,其结果则造成了“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的十年浩劫。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法治”的前身“法制”才登堂入室,成了座上佳宾。而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条基本方针后,民主与法治这才正式携手,成为官方和学界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话语。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宪政民主简单化理解和误读,对于法治作为宪政民主的前提性地位茫然无知,在客观上造成了实践过程中民主与法治发展的历史错位现象,其后果必然是‘德先生’在中国的命运坎坷多艰。”
从结构特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是是一个综合的制度体系:既强调民主,又注重法治,进一步表现为民主与法治之间保持一定张力的均衡,成为政治文明两个最基本的维度。因此,民主与法治在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
由此可见,能否实现民主的制度化与权力运作的法治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能否持久的核心问题。然而,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困境就在于,“法治和民主在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共存。建立强权政治意识以及强权式的民主制度很容易……但建立法治观念和法治制度极为困难”。 我们从那些民主进程遭受挫折的国家最应该汲取的教训就是“民主运动”式的激进改革并没有带来国家的真正民主化,没有法治的制约,单纯的民主是脆弱的。
而不论“民主运动”式的激进改革还是建立强权式的民主制度,其思想根源都是源于民主迷信,甚至是“图腾式”崇拜(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领袖个人品质问题的话)。从这个意义上讲,潘维先生所言实在是一语中的。“直到18世纪,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民主是什么,可几乎没人支持民主制。现在则倒了过来,所有人都支持民主制,可再也没人知道民主是什么。” 透过这句话,或许我们不难读懂作者的心境。
六、余论
通过上面的分析,笔者自己已经差不多被潘先生的观点说服了,然而斟酌再三后,还是觉得有若干“白璧微瑕”,虽无伤大雅,但还是指出为好。
在论及“法制”与“法治”的关系时,潘先生将前者解释为“法律治国”,将后者解释为“依法治国”。 这样理解不仅不符合法学界的通说,而且很难据此对二者进行区分与辨析,给人以 “越描越黑”之感。其实,在今日法学界,在这两个语词的含义上大做文章早已成了“昨日黄花”,直言其为“没意思”者也大有人在,更何况这两个词也并不是不能做可通约的解释。但是,既然潘先生在文中指称二者有“本质的不同”,那就应该对其进行本质上的清晰界定,如此方能自圆其说,而其现有的说法则明显缺乏解释力。
再者,潘先生在书中数度采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来对中国官方权威政治文本进行解读,在这一点上可谓令人拍案叫绝,因为中国主流政治话语向来惯用“春秋笔法”,常以“微言大义”示人,如能深入解读、详加剖析,往往有意外收获。如他将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表述解读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已经有的,仅需要‘坚持’和‘完善’;但‘社会主义法制’确是需要‘建设’的,而且要‘加强’建设。” 真可谓“号脉准确”。不过,潘先生似乎忘记了“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的道理,而贸然将邓小平的“(香港的制度)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后是不需要变。”解读为“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就是这样婉转的表达了他对香港制度的坚定支持以及对‘五十年后’内地政体的殷切希望”,并据此将邓小平的政治观点定位为:“明确反对把民主制引入中国,数番表达了对香港政体的支持”。在这样一个理论预设下,他的解释当然很巧妙,也恰好为其推崇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代表的“咨询型法治”提供了论据。但是否真的符合小平同志的本意呢?其实,邓小平支持香港的政体的初衷已经在潘先生的文中被“婉转的表达了”——“在行动上坚决抵制了彭定康将香港政体民主化的企图”。 可见,老人家是为了能让香港顺利回归,避免出现动乱局面才作上述表态的,其背后更多的是一种“对策性”考量。将其理解为对中国大陆未来政体走向的预示和期待,虽不可断然否定,但至少是缺乏论证的,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而将小平同志归为“明确反对把民主制引入中国”则更是冤枉乎哉!邓小平确实反对照抄照搬西方式的民主,主张民主建设应该根据中国国情循序渐进的进行,但他从来不否认民主的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就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他不仅向委员们承诺“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不需要变”,而且还告诉大家:“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这难道就不是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殷切希望”吗?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中国的问题,就应该“比从前更加认真地对待政治领袖的著作,而不能为了增强自己理论的合理性、追求‘政治正确’而随意‘剪裁’”,更不能“仅仅为验证某个别国的成功模式而作适应性研究”。
尽管存在上述不足之处,但潘先生所论之问题——“民主迷信”现象——却仍不啻为“振聋发聩”。常言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信仰甚至“迷信”任何一种“民主”而不问其“出处”,但若是其作为一种价值观乃至一种企图在我们念兹在兹、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土地“试验”的,关系到亿万人身家性命的政治体制来“推销”和“兜售”时,我们可别忘了问上一句:请给个理由先!
金钊,男,现求学于湖南大学法学院,E-mail:kingjzmao@yahoo.com.cn。本文已刊于《岳麓法律人》杂志(第二期)。
参见[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3年版。
[法]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
黄炎培:《延安归来》,转引自李步云:《关于依法治国的几个问题》,载应松年主编:《法学专题讲座》,: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366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毛兴贵:《自由主义:普遍的抑或多元的?——读<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载《书屋》,2003年05期。
参见马宝成:《政治合法性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8页。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页。
[美]拉里•戴尔蒙德:《第三波过去了吗?》,载《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4页。
参见郝铁川:《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载《中国法理学精萃(2003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美]马克•普拉特纳:《自由主义与民主:二者缺一不可》,载《民主与民主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同上。
许章润:《不能拿“结果”做“起点”》,经济观察报网站 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3396。
[法]米歇尔•克罗齐,[日]绵贯让治,[美]塞缪尔•亨廷顿:《民主的危机》,马殿军等译,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美]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载[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1页。
周旺生:《中国立法五十年》,北京大学立法学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pku.edu.cn/academic/legislation/zwslw/zwslw_zhglf50.htm。
同上
麻宝斌:《论民主的法治前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
潘维:《法治与民主迷信》,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第21页。
同上,第143页。
同上,第140页。
同上,第193页。
同上,第45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见拙文《会不会又是在“等待戈多”——对当下“宪政热”的冷思考》,载《岳麓法律人》(创刊号)。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