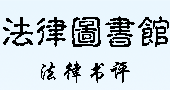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缺月》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陈鸿彝 2007-1-1 11:03:28
看《缺月》,说随感 陈鸿彝青年作家穆玉敏同志的新作《缺月》问世快半年了,各方反应热烈,尤其是在警察队伍内部,亲眼看到了自己人写的贴身事,自然有一种亲切感与真实感。这是一个可心的载体,透过它,警察及其亲人心中积之已久的那份酸甜苦辣、那份悲喜忧思,那种对于社会理解的热切呼唤、对于感情回馈的深切期盼,终于有了个疏泄的管道。这种舒坦,局外人是不易体察的。
(一)
读着这本书,我总在想:“缺月”,与其说是全书的结构线索,莫如说是它的精神象征。作者属意于缺月而欣然取象于它,自有一番深意在。
缺月有两种:一是正在走向圆满的新月,它总是带着希望与激情,临空普照,逗引着人们的新奇与喜悦,让人翘首,让人雀跃;一是由圆满而陷入偏缺,它必定要经历残毁甚至沦丧,而它所引发的则往往是“低头沉思”。人们相信,它正在艰难竭蹶之中孕育新生,它有韧的生命力,它会嬴得“明天”(或曰“明夜”)!是的,当今的生活中,不乏新奇,倒是更需要沉思。缺月在树稍,让我们多一点静心的思索,多一点对于生活真缔的寻绎。
作者说:太空本无所谓缺月,月亮从来都是圆的;缺月,那是特定地带的人群所感知的一种视觉形象,只是月轮闪亮面的一个“侧影”。你以为有“缺”,殊不知,那被忽略了的另一部分,同样真实地存在着,那叫月魄!只有“闪光的”与“养晦的”两部分的结合,才是月华的整体 ----哦,我懂了:真实的“月”,无所谓“缺”,从来如此,而生活本来也就该这样:有显现的,也有隐蔽的;有明洁的,也有灰色的;有炽烈耀眼的,也有静默自守的……真有意思,在中外诗文长廊里,“月相”纷纭,可有谁见过这样的“月”:它“缺”着,也“完整”着;它的“缺”,引人注目,让人端详;而它的“完整”,却有待慧眼去发现,去确认;有待情灵的体味与思考。看着《缺月》,我一面欣赏着作者对月魄的把握,一面品味那多维的人生。
“缺月”,作为圆月的一个“侧影”,它自有其独特的美!
(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革命理想”、“党的儿女”这些词汇,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古老传统似乎“决裂”了;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公无私”、“革命理想”、“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些词汇,也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现实生活,正如书中主角陈素娥所困惑的:“过去讲跟党走,讲牺牲,讲奉献,如今这些都过时了,谁提谁就是傻瓜。难道我真的跟不上趟了?”而《缺月》,显然是带着这沉重的思考,在呼唤“传统”的归位与更新。
书中写了三代以“月”命“名”的女性:陈素娥--韩玉镜—董新月。她们成长的“社会文化场”不同,生活经历不同,个性色彩不同,却有着相同的灵魂、一致的“月魄”:她们都痴情于真爱,执着于承受,自主于奉献,又都懂得在神圣信念面前的贞守与操持;她们都在用自己的生命演绎着只属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传统:民族的又是革命的,承袭而来的又是全新浇铸的,社会土壤的又是党的儿女的。
陈素娥:出生于塞外人家的一间茅屋里,茅屋的家主早年在跟日本鬼子的拼杀中牺牲。共和国成立时,她十七岁了,妈妈让她嫁了个并不相知的大男人。这男人是在城里当警察的,这个警察把事业干得轰轰烈烈,十天八天见不着人影儿,想疼她却没功夫疼她,倒是让她懂得了什么叫“服从革命需要”;她呢,想帮帮男人,却插不上手,就尽力免除男人干革命的后顾之忧,很快又有了爱情结晶“宝宝”,生活的彩卷正在打开……不成想这男人天生是“公家人”,不久便成了共和国公安战线的“第一名革命烈士”。男人没了,她伤心极了。市政府接她进了城,让她住进了一座有高门楼子的大宅院,门楣上贴着“烈士之家”的牌牌,室内墙上贴着烈士遗像,天天有人送来慰问、关切、温暖、荣耀,远远近近的中学、小学、街道、工厂,都来请她去讲丈夫的英勇事迹,忙得她顾不上想自己的苦,也不敢在人前哭。夜深人静,她对着遗像发呆,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晴却对她说:“娥,咱不难受;咱有政府,有亲人;你要对得起党给的这份荣耀。咱还有后代,你得把他养大,让他接我的班。”她想:“是了,孩子是烈士的后代。你不是叫“罗静风”吗,那就让孩子叫“罗继风”吧!”于是,她抬起头来,抹干泪水,跨出家门,走向社会,成了一名地道的革命宣传员和刚强的社会活动家,街道上人称她为“革命妈妈”。一月两月,三年五年,烈士遗孤成人了,她把他送去接班从警。儿子挺争气,总能立功受奖,她享受着养儿成才、英雄有后的幸福与慰安,忙得更加有声有色了。不料,这一天,她接到了儿子死于非命却又死因不明的噩耗……她伤心欲绝,但一个信念支撑着她:“我丈夫是英雄,我儿子决不会是狗熊。我这个做妻子、做母亲的,就应该像模像样地站着,决不趴下!”于是,她承受着,她坚持着,她以革命的名义判断是非,她以烈士的精神要求自己,在深深的怀念死者与苦苦地贞守光荣的岁月中,她跋涉前行,随时跟旧有的、新生的腐臭与卑污作斗争,决不让“烈士之家”的门楣有亏;至于那个千里以外赶来缠上儿子的女大学生,则决不让她再登家门。
生命,在她,天经地义地是属于革命的。
韩玉镜:生长于安徽的一个知识家庭,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代女大学生,既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又有对“家教”的某种“叛逆”。一个偶然的机会,英姿奕奕的青年民警罗继风吸引了她,她兴冲冲地来到塞外山城“访友”,两颗年轻的心碰出了火花,她憧憬着自己的烂熳未来,盼着有机会向自己的所爱、也向山城父老奉上一分力、一腔血、一颗心…… 谁知,那位深深爱着她的青年民警,竟然连给她一个正当的“名分”也来不及,就被一群“人渣”抛尸荒野,谁也不明白其中曲折。她这片飘来的红叶,而今䒮䒮孑立,举目无亲;生活猛然向她打开了深邃无边的大门,她毫无准备。那位“革命妈妈”又大义凛然地拒她于千里之外,自己的亲娘也因为她腹中有颗不期而来的“种子”而与她生死两绝。她本无心于触动现存的生活秩序,而秩序却如此地容不得她。她深知自己的无脸、无助,也无“法”、无“理”、无“路”去弄清楚罗继风的确切死因,但她确信心上人死得正大。从此,她只得独自苦挨着,偷偷地躲到陌生乡下去悄悄地生下他的遣腹子,特意起名叫罗小风:这是她的、也是罗家的惟一的希望。在那间乡村小学里,她含辛菇苦,尽心尽力,蒙受着人前人后的指指戳戳,要把儿子拉扯大,期盼着寻回死者清白的一天。然而,这儿非久居之处,她只得孤身到万里之外的边城去另觅生机。苍天有眼,正涌动着改革开放热潮的边城接纳了她。她凭着惊人的生命力,在“开发区”的大潮中乘势而上,她直面色彩斑斓、让人眩晕的外部世界,竟然无本起家,真的闯出了一片属于她自己的天地,成了一位名扬境内外的“女企业家”,还把儿子送进了警察院校……这一路走来,她苦呀,她承受的坎坷、磨难,孤寂、失望,比谁都多,可她仍坚守着私下独自认可的“革命伴侣”、“英雄亲属”的“本份”与“本命”,做自己想做的事:非得让儿子罗小凤成长为罗静风、罗继风式的男子汉不可。她也真的达成了所愿:以一生的承担化解老一辈的误解,找回同龄人的失落,赢得新一代的尊重。
付出在我,理解由人,活活一代善良女子的韧的生命的剪影,又何尝不是罗家献身精神的另一版本的演绎!
董新月:改革开放中出世,改革开放中长大,改革开放中从警,也就在改革开放中担负起“物证鉴定”的一份辛劳。她凭借着女性的精心和专业的敏感,分享着战友们“保一方安宁”的神圣与崇高;刑侦勇士那浓烈的阳刚之气便悄悄地薰染着她,她被吸引了。当她和他(刘正刚)彼此感触到对方的呼吸与心跳时,立刻放射出倍加绚丽的七彩之光。这基于“一个战壕”里自然成熟的“爱”,凸显着新时代“同事加朋友而终成恋人”的坦荡与纯真。她和他,没有时间去卿卿我我,甚至省略了许多爱的伪饰与遮掩;却也少不了手牵手、肩挨肩、心对心的触电机会。他和她少了点浪漫性传奇色彩,多了些职业性的节制与关爱——连新婚的手续也是在业务忙碌的夹缝中请假去办的——却拥有天底下一代新人的最大幸运:她没有陈素娥婚前的陌生与隔膜,也没有韩玉镜婚前的煎熬与挫折,等着她和他的只是二十个小时后就要举办的“新婚典礼”,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她心头溢满了幸福。但是,且慢!生命的另一半没等到与她“结合”却突然逝去!这一惊天一击,粉碎了她对幸福的热烈期盼;然而,她是坚强的,她和陈素娥、韩玉镜一样:一样从悲哀中挺起身来,一样去迎接生活的挑战,一样要以全新的业绩来告慰亲人加战友的在天之灵。她绝不让悲痛压垮自己,而要继承遗志,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实现自身价值的升华。所幸的是:她和陈素娥、韩玉镜不同:生活不再会给她莫名的沉重压力,周围也不再会有那种无故的冷漠与排斥,贞守革命情操也不必再以孤寂终生为实践模式,她可以意气风发地去张扬生命的华彩。于是,她踏上了拜访全国烈士遗孀、遗孤、遗族的长路,承担起沟通警民心灵之桥的重任,她要激活珍藏于或者潜沉于社会良心深处的对革命者、对奉献者的崇敬与膜拜,和战友们一起,去合力营造明天。
她、她和她,都是党的女儿,都有我们这个民族的善良与坚韧。她们或许是缺月、残月,或许是一弯新月,却都内蕴着民族传统、革命传统的伟力,她们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持续存在、生生不息的土壤,才是我们事业的最后依。
(三)
作者是善于结撰她的故事的。三十万言的长篇,没有按事理自身的历时性轨迹去叙述,不以情节的离奇起伏来吸人眼球,不以题外的说教来换取“正统”的“通行证”,更不靠厮杀拚搏、黑厚奸拐来搞强刺激;而是按主人公情感色调的交替晕染、晖映互渗的法则来剪裁素材,让事实自身含蕴的情感直诉于读者的良知,去垂击读者的心灵,让你在泪光中照见自己的灵魂,从而获取应有的精神反馈。
本书的情感基调无疑是严肃而沉重的,但它首先推出来的却是董新月与刘正刚的甜密的爱,亮丽的情,坦然的心,和警察生涯中特有的紧张所烘衬出来的新婚来临之喜。唯其如此,刘正刚的突然蒙难,才给人以晴天霹雳般的震撼;由此而磨击出来的新月之光,才有了穿透世俗判断的锐利,让人看到了指向男女警察心灵深处的特色通道。
韩玉镜和罗继风的爱,被置于省城刑侦大队侦破沈含章命案的胶着求解之中,她们爱得稀奇,爱得炽烈,爰得纯真,甚至有点儿“出轨”,却又毫无功利的计算;浓情的爱与刑侦队上下有序的工作进程以及一定程度的焦灼心态相交映,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又与老一辈贞守的传统规制与革命情操大异其趋,于是幻化成一曲激越的奏呜曲。开卷至此,读者的心弦又怎能不随之起伏?为他们祈涛吧,祈祷两个生命的幸福结合,也祈祷一宗命案的早日侦结。
陈素娥与罗继凤相结合的行事方式,是那个时代很正轨、很普通、很符合民风民情的要求,从而也是很典型的一例:先结婚,后恋爱;守了寡,不变心。如果按照历时性轨迹来叙述,这情节本来应该是最早叙述的对象,但作者没有把这些已经成为“轶事”、“趣话”的话题放到文首,却放在董新月征求“烈士遗物”的过程中娓娓道来。作者让主人公的带着些许辛酸的“轶事”在时过境迁的场景下叙来,例如新婚夫妇不得不租宿小旅舍来且度良宵的故事,例如强忍着丧夫之痛、抹着眼泪去当众追诉英雄舍身忘死的情节……这类往事就变成了新时期催人奋进、引人深思的“情感添加剂”。不知作者是否深明“酒道”:愈是陈年老酒愈能透出阵阵醇香。
罗静凤的战友与上级、罗继风的“发小”与同事,韩玉镜的相识与相知,董新月的战友与领导,加上那位小小年纪的罗小风,在上述三代人的情感历程中,作为英烈见证人、苦难目击者和激情助燃者交替登台,为三代“缺月”映彩增辉。从文字铺排上看,该不是作者剪裁缝合术的妙手偶得吧?
(四)
随笔到此,还想跟作者说几句:本书对“时代文化场”的勾勒有独到之处,比如陈素娥忙着宣讲英雄事迹的风光,比如韩玉晶初到山城时的欢跃与乡村任教的艰辛,比如董新月从业之时的认真投入,都写得很实在,很精彩;不过,也许是“警察”的独特眼光使然,也许是破案题材固有的局限,使作者的目光总是集中于“出事”的环节上,而对“大背景”的描摹则显得笔力不足。记得吗?那家破旧零乱的汽车拆解厂,那座光怪陆离的境外赌博场,那片深夜搏击的沟坎地,笔墨何其真切细致,几乎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而相形之下,对于“大时代的大气候”的表现,则显得单薄了许多。于是,韩玉镜的之所以成为企业家,就显得“抽象”,还不如王横宽的得意、得手来得“可信”;张威宁在商品风潮中的心灵扭曲与变迁,就比沈含章在事业上的不懈奋斗写得具体可感;而那位甄珍在政府机关的一场大闹,其个性表现的力度就远大过董新月的长年奔波……
或许,是我过虑了。若照我想的去写,本书就不是本书了。大嘴巴说着玩儿,过过嘴瘾,想来是会得到谅解的。反正批评人不犯法,是吧?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