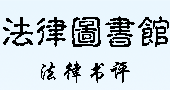初识法人类学《初民的法律》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张敏 2006-11-23 10:51:38
一、霍贝尔先生简介霍贝尔先生(E. Adamson Hoebel,1907-1993)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法人类学家,研究原始法的权威。他早年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后来在明尼苏达大学任人类学教授。他曾作为“东西方文化中心”(the East-West Center)的高级研究人员,并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从事研究。
霍贝尔先生的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科曼奇印第安人的政治组织和法律方式》(1940年)[1],《切依因纳人的习俗》(与著名法学家卡尔·卢埃林合著,1941年)[2],《运用于原始法研究的基本法律概念》(发表于《耶鲁法学杂志》,1942年)[3];曾与另一位学者合作,翻译了荷兰法人类学家哈尔的经典名著:《印度尼西亚习惯法》[4]。
《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The Law of Primitive Man——A Study In Comparative Legal Dynamics)是霍贝尔先生的一本力作,为作者带来了很高的学术声誉。该书初版于195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欧文·卡普兰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称:“这本书是对我们所知的原始法总检讨的最佳作品……它适读于人类学者、法律工作者和职业社会科学工作者……”《耶鲁法学杂志》刊登了伦哈德·亚当的评价:“这本著作肯定会成为将来社会人类学和法理学学生学习原始法的教科书。”[5]据罗致平先生在该书中译本“校者前言”里介绍,此书问世后,一直印行不衰,被陆续译成德、意、日等多国文字,其日文版的译者千叶正士和中村孚美两位教授将书易名为《法人类学的基础理论》。该书的学术地位,由此可略见一斑。
二、《初民的法律》一书的概要介绍
全书的内容分三个部分,含十二章,依次是:第一部分,“原始法的研究”,第一至四章;第二部分“原始法的几种形式”,第五至九章;第三部分,“法律与社会”,第十至十二章。作者在“原序”中说,“本书在论及法和人类学的安排上,首先将阐述一套思考和研究初民社会的法的方法。第二部分,参照重要的司法前提原理,以及它们转换成法律形式和行为的方式,来分析七种原始文化”;第三部分对法的功用等宏观问题作了综合性的研究。以下笔者拟简要介绍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讲法的文化背景。法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特定社会的法离不开对相应文化的把握和理解。社会选择理论奠定了作者行为主义研究的基础:每个社会必须在其文化中选择数量有限的、能密切配合的行为方式,并拒绝相反的行为方式,但留有弹性。(页12-13)作者采纳奥蒂斯·李关于法的前提原理理论,以此塑造案例研究方法,并贯彻于本书始终。这一理论的要点为:(1)每一种文化,均代表着一个个人的或集体的从整个人类潜在可能的行为方式中所作的一种有限的选择。(2)选择依据前提原理作出。(3)社会均有一套完整而连贯的行为方式、组织结构或人际关系的制度。(页17-18)
第二章,要给“法”下个定义。首先,明确了法有三个特征:
(1)特许的强制力。“威胁使用或实际运用人身的强制,是就一合法的原因,用一合法的方法,在一合法的时间内,由一有权力的主体来行使。这使法律的制裁同其他的社会规范相区别。”(页28-29)
(2)官方的权威。指“普通或特别认可的作为合法行使人身强制的人,是社会权威的派生。……他不是也不可能仅代表自己、他的家庭或其氏族而行为,他享有该社会与此案无利害关系的其他社会成员明示或默示的支持。”(页29)
(3)常规性。它是法与一切其他的文化规范所共有的属性。
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经典的法的定义:“法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当它被忽视或违犯时,享有社会公认的特许权的个人或团体,通常会对违犯者威胁使用或事实上使用人身的强制”。(页30)
霍贝尔的定义,堪称法理学界对法的经典表述之一。这个定义采取了行为主义的视角,代表了人类学家对法的认识,是法人类学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个定义在法学著作,尤其是法人类学和法理学著作中被经常提起,并为国内外法学家所津津乐道。有的学者在其文章的开头,将霍贝尔的定义与韦伯的定义相提并论,作为具体研究的理论前提,[6]可见霍氏定义的份量。
第三章,确立案例研究方法。与前人采用的理想规则研究方法(做问卷调查)和描述研究方法(民族志写作)相比,案例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1)避免法的抽象化、形式化,与现实的生活紧密相联;(2)以研究纠纷解决为中心,在关注实体法内容的同时,也重视程序法问题。案例研究方法的倾向是归纳,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从众多的案例分析中求得原始法的规范。“这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个从特殊到一般,再通过对一般的进一步检验回到特殊的过程。”(页38)从本书的写作上来看,案例研究方法在原始法研究中的运用,基本上表现为首先归纳提出十来个某个原始文化的前提原理及其推论,然后依具体的法律问题用比较详细的实际案例阐释前提原理的规范机制。依笔者的理解,这些前提原理是特定社会中若干最重要的文化规范,类似于我们现代人熟悉的宪法规范。
第四章,采用霍菲尔德(Hohfeld)理论作为原始法研究的术语体系。霍菲尔德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分析法学派代表人物,代表作为《在司法推理和其他论著中所运用的基本法律概念》(纽黑文,1923年)。霍菲尔德认为,一切法律关系都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每个法律关系都是双方面的,可以化解为最基本的四组关系,用八个基本法律概念来表述:
甲方 乙方
(1) 请求权(Demand-right)————义务 (Duty);
(2) 特许权(Privilege-right)————无请求权(No-demand-right);
(3) 权能 (Power) ————责任 (Liability);
(4) 豁免权(Immunity) ————无权能 (No-power)。(P.51)
霍贝尔先生是霍菲尔德理论的追随者,认为霍氏理论具有以下优点:(1)用霍菲尔德的概念来描述原始材料是可行的;(2)这种描述方法增强了人们对案件的感性认识,更明确了所在的问题和含义以及法律上的有关限制;(3)运用霍菲尔德的概念来替代一切过于宽泛的和不恰当的术语词汇,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执和混乱,例如关于某些原始的财产形式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纠缠。(页59)
第五章,研究爱斯基摩人的法。爱斯基摩人约有2万人,分布在北美北部沿海地区,依靠初级的狩猎谋生,主要捕杀海豹、鲸鱼和驯鹿。爱斯基摩人形成若干地方群体,每个地方群体包含约12个家庭,人数往往在100人以下;各个地方群体之间鲜有交往。在爱斯基摩人社会里,宗教禁忌很多,规范着人们方方面面的生活。前提原理之一为“生活艰难,维持生存的水准很低”。由此,就不难理解:杀婴、杀病残者、杀衰老者以及自杀,都是行使特许权的行为,它们是社会认可的杀人。
爱基斯摩人可能是迄今所知最为原始的初民社会,其世俗领袖的产生情况对于研究公共权力的诞生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头人就是那些善于打猎,‘熟悉传统、习俗、节日仪礼,并远远超出公众的一般水平,以及作为该社区的主要领导者,他的意见为公众听从并遵照执行的人’。这就是在未开化的人类社会中政治权威的萌芽。”(页89)
杀人往往起因于两性关系的混乱,血亲复仇得到社会的默许,然而杀人惯犯却是社会的极大公害,须被清除。“一次杀人的行为是一种私法上的过错,由被害人的亲属予以补救;多次犯有杀人行为的人,则被视为危害公共利益的罪犯,由该社区的代理人将其处死。”(页96)
斗歌是爱斯基摩人最出名的纠纷解决方式,可以适用于解决杀人以外的一切纠纷,通常多为通奸案件。纠纷当事人亲自或者托人运用传统的曲调格式,将己方的控诉或辩解编入歌词,当众高声宣唱,并可以添加插科打诨式的滑稽动作,丑化对方,或者相互以头抵撞,以求赢得观众的热烈喝采。其结果并不给胜利者带来任何经济上的补偿,唯一的得益是个人社会威望的增长。斗歌在其用来解决纷争和恢复该社区内冲突双方的正常关系时,是一种司法的手段。它使当事人借此发泄了怨恨之情,心理平衡重新恢复。“如同爱斯基摩人所认为的,这就是爱斯基摩社会所需要的足够的正义。”(页108)
第六章,研究伊富高人的法。伊富高人是居住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经济上以精耕细作、灌溉锄耕的农业文化为中心的原耕民;人口约7万,尚未形成部落。根据作者的归纳,伊富高社会的一项前提原理是:稻米是一种好食品。挺有趣的。
在伊富高人的纠纷解决机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调解人(“蒙卡卢”)的参与和作用。
第七章,研究平原印第安人的法。科曼奇人、基奥瓦人和切依因纳人都是北美平原游牧部落,可归为较高级的狩猎社会。这三个部落所处的地理环境、经济方式和文化习俗十分接近,但是依据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程度,其社会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切依因纳人,基奥瓦人,科曼奇人。作者是平原印第安人研究的专家,曾亲自从事对科曼奇人和切依因纳人的富有成果的田野工作,并列这三个部落并加以比较,旨在探究影响社会规范体系发达程度的其他因素。
就切依因纳人而言,其部落中已出现较为正式的管理机构:(1)部落议事会。由44位首领组成,实行推举制。议事会的传统权能是处理杀人和通奸案件引起的纷争。(2)军事会社,又称战友会。其职能主要集中于维持共同狩猎和部落大型仪礼活动时的秩序,而且随着现实发展的需要而渐有扩展。
切依因纳人坚信,杀人会玷污部落魂灵(神秘的表现为:圣箭出现血迹),导致厄运降临部落(例如交战失利、出猎无获);而且杀人者是不祥之人,尽管看起来健康完好,但“内脏腐烂”,“发出恶臭”,致使猎物逃避。因此一旦出现杀人的情况,部落仪事会就要举行圣箭更新仪式,洗涤罪孽,全体成员必须到场,由军事会社负责维持秩序。反杀复仇也是杀人,受禁止。议事会将流放杀人者,而不能执行死刑;至少5年以后,才会考虑重新接纳被赶出部落的杀人者。作者对切依因纳人的社会控制体系评价很高,称赞切依因纳人仅仅凭借宗教上的观念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困扰众多初民社会的世仇反杀问题。
作者曾与卢埃林教授合作撰写《切依因纳人的习俗》(1941年),引入案例研究方法,取得极大成功,开创一代风气。本章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切依因纳人的习俗》一书的研究成果,对案例研究方法的贯彻较为充分。
第八章,研究特罗布里恩德岛人的法。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系列民族志和理论著作,是最基本的参考资料。作者高度评价马氏作为一位人类学家的学术洞察力,叹服于“马林诺夫斯基仅在平静的环礁湖上航行就触及到了法律”。(页202)马氏对原始法和法的一般理论怀有持久的兴趣,著作不断,被认为是法人类学历史上的一大关键人物,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最重要的法人类学家,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7]针对马氏的法学观点,作者阐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交换食品竞赛(“布内贴拉乌罗”)是特罗布里恩德岛人颇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方式。
第九章,研究阿散蒂人的法。在非洲西部的黄金海岸,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阿散蒂人建立了一个大众的军事国家,城市和乡填具有除文字以外的一切初生文明的因素。阿散蒂人已形成拥有20万人口的部落联盟,其首领的地位相当于国王。一旦君主制得以确立,人们便越来越多地将解决纷争的功能交由行使权力的第三方即君主制国家承担。阿散蒂社会禁止反杀和世仇,“只有国王才可以掌握刀把子”。(页262)其不成文的刑法已发展至相当规模。
阿散蒂社会实行世袭的君主制,但国王从其作为王室候选人之时起就要受到多重限制,违背规矩和诺言的后果将是废黜,类似于一种君主立宪制政体。
从第十章起,就进入了本书的第三部分。第十章,研究宗教、巫术和法律的关系。理论界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即法起源于宗数,而且认为这是梅因在《古代法》中的一大发现。作者却不以为然,认为是后人附会了梅因的原话;法与宗教同属社会规范体系,有各自的调整对象,互相作用,联系密切,但还不足以推出法起源于宗教的结论。笔者以为,依据现有的资料,不难发现法与宗教的关系是一种结构性因果关系,正如作者描述的那样;要证实法起源于宗教——此时,法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须是一种线性因果关系——这一命题,尚缺乏足够的依据。
巫术与宗教不同,且有好巫术与邪巫术之分。邪巫术与法的关系是互为消长的关系,而好巫术却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辅助法律的实施。
第十一章,研究法的功用。作者引用《切依因纳人的习俗》一书中的研究成果,指出法有以下四大功用:第一,规范人际关系;第二,规范社会强制力;第三,处理纷争案件;第四,当社会的情势发生变迁时,重新限定或规范人际关系。(页309)
作者进一步归纳了在各种原始法中普通存在的若干前提原理,例如:巫术宗教的力高于人类,而且神灵也具有与人类相同的情感和理智;社会中的杀人行为在一定的条件下都是为法律所禁止的;每个社会都相对贬低妇女的社会地位;一切法律制度都将某些物品确认为私有财产,而土地很少被视为私有财产,等等。(页321-322)
第十二章,研究法的发展趋势。梅因的《古代法》中有一句名言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我们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页368)据此,法人类学家们认为梅因是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而霍尔贝先生在研究类似的主题——法的发展趋势,他因为变化和例外如此频繁,以致于拒绝使用“进化”一词——时,基于对原始法的渊博知识和深刻认识,提出了超越前人的全新观点:“在原始法的发展过程中,真正重大的转变并不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实体法上的从身分到契约——尽管这是欧洲法在其后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而是在程序法上所发生的重心的重大转移,维护法律规范的责任和权利从个人及其亲属团体的手中转由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政治机构的代表所掌管。”(页369)简言之,法的发展趋势(或进化),集中体现为程序法上发生的重心转移,即私力救济逐渐为公力救济所取代。根据这个观点,研究者们将霍贝尔先生归为新进化论者。[8]
笔者以为,霍贝尔先生关于法的发展趋势的论点,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具有更宽广的适用性。作者在为前人所忽略的程序法研究领域里,发掘出一条人类法律文明演进所遵循的基本规律,并为衡量一个文化的文明程度提供了一个明晰的尺度(可作为众多尺度之一)。与梅因的观点相比,能够对霍贝尔该论点证伪的例子,恐怕更难以寻找。霍贝尔先生的发现,有其背景:第一,整个法人类学的研究重点经历了一个以实体法为中心,到兼顾实体法和程序法,再到以程序法(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发展过程。霍贝尔先生大致处于中间阶段,不再忽视程序法问题,而且在研究法的发展趋势时,能够敏锐地把注意力集中至程序法上的重心转移。这对于其后法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转换,不无影响。第二,程序法更适于作比较研究,更易于在动态历史比较下展现其内在规律。实体法的内容包罗万象,难以明确具有可比性的问题,因而现有的实体法研究难免显得纷繁零碎,进展有限。而程序法相对内容较为集中,人们容易从中发现可供比较的问题,于是程序法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成果不断积聚,为开展全面的比较研究提供可能。第三,与作者对法的定义有关。假如把法的核心特征界定为须由某种形式的社会性机构(例如法院、国家)行使强制力,那么原始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私力救济现象就根本无法进入法的范畴。而作者对法的定义(页30)则宽泛得多,仅要求行使强制力的主体“享有社会公认的特许权”,包括个人和团体,从而大大拓展了法的外延,使其涵盖私力救济现象,为发现法的发展规律奠定了基础。
在本章的最后,也是全书的结束部分,作者呼吁法学家和人类学家要致力于建设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世界法。他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就其功能的发展水平而言,仍然是最原始的部落;所谓的国际法,只是世界范围内的原始法,因为国际法中的实体规范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页371-372)作者不忘将现代国际社会与原始社会作比较,表明其对法人类学的任务和意义的认识。
三、原始法研究三大问题之我见
(一)关于法的本质
霍贝尔先生对法的定义,是运用人类学方法和成果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影响较大,知名度很高。笔者以为,霍贝尔对法的定义,对于本书范围内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
第一,由此推导出原始社会也存在法的结论。原始社会是否存在法,是不少法理学家争论良久的问题。其实,答案在于对“法”下如何的定义。许多原始社会中根本不存在法院或类似专司纠纷解决的公共机构,假如把法的核心要素界定为此类机构,法学家对原始文化的研究很可能会一无所获。而作者对法的内涵的界定,为将原始社会中的某些社会规范现象纳入法的外延打下基础。
第二,依此区分习惯与法。习惯与法的关系如何,是本书研究“法是什么”的出发点。针对前人主张法等同于习惯的观点,作者先是举如厕训练、制陶、握手行礼等习惯为例来反驳,中间虽然未对习惯与法的关系作集中而明确的分析和阐述,但根据最终所下的法的定义,法与习惯的区别自然不辩而明了。
第三,据此发现法的发展规律。这一点,笔者已在第十二章内容简介里作了说明。
学者严存生认为,霍贝尔“在对法律的理解上,过分强调了强力的作用,而且混淆了国家和其他强力的界限,因而把一切以强力为后盾的社会规范统统称之为法律,从而得出原始社会存在法的结论”。[9]笔者以为,严存生的这一批评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关于法的本质和定义的观点。依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界的通说,“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10]这个定义反映了法的规范性、国家强制性、阶级意志性和物质制约性。此外,法随着阶级分化、国家产生而产生,在国家尚未出现的原始社会里,法无从谈起,而只有习惯调整人际关系。由此可见,霍贝尔与严存生的理论出发点不同,双方的分歧源于对法所作的不同界定。笔者认为,理论研究不排斥多样化的理论界定或理论假设,但特定的理论界定或假设必然有相应的适用范围。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有助于解释阶级社会的法律现象,而霍贝尔的理论则更能涵盖阶级社会之前的原始社会。因此,两者的分歧是难免的,而且这种分歧的意义十分有限。
至于霍贝尔先生对法的定义的不足,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两端:
第一,继承为主,创新不多。霍贝尔的定义基本上以大法官卡多佐对法所下的定义为蓝本,而稍加以改进。卡尔佐对法的论述本身就是一种经典:“法是这样一套确立了的行为规范或原则,它能够在适当的、确定的情况下,预言何种行为是正当的。如果其权威受到了挑战,它将由法院强制执行。”(页23)在这一定义中,法具有四个基本要素:(1)规范的因素;(2)常规性;(3)法院;(4)强制。与卡多佐的定义相比,霍贝尔的定义只是以“享有社会公认的特许权的个人或团体”取代了“法院”这一要素,而承继了其他对法的特征表述。霍贝尔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又向前迈了一步,既未突破已有的理论框架,又未开创新的界定视角,成就有限。
第二,对法的本质缺乏系统化的研究。对法下一个精炼的定义,历来是法理学的一大难题,难就难在要想知道法究竟是什么,必须首先清楚法不是什么,即必须明确法与道德、宗教、权力、习惯等其他社会规范体系的关系,尤其是彼此的区别和差异。在本书第二章里,作者仅涉及了法与习惯的关系(而且并未给予明确、直接的回答),根本没有讨论、研究法与其他社会规范体系的关系,而是径直就法的组成要素展开对法的本质的探讨,并给出了一个定义。可见,作者对法的本质的研究忽略了一系列的基本问题,是片面的,由此获得的定义缺乏系统化研究的支持。
(二)关于案例研究的方法
作者一再强调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确立其为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对以后的原始法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者如此推崇案例研究方法,与以下背景事实有关:
(1)普通法的传统。美国法属于普通法系(又称英美法系或盎格鲁--撒克逊法系),继承了判例法传统。法院作出的判决对以后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具有约束力,即遵循先例原则。判例包含了法的原则或含义,成为法官可据以裁判的法律渊源。普通法的法官须接受正规的法学教育,掌握准确援用判例法的区分技术。判例法传统明确支持“法官造法”,并且引以为豪;法官们稳健地在判例中提出新的规则,推动法律的发展,使之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判例,即有法律约束力的既成案例,在普通法国家的法律生活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案例教学构成其法学教育的特色内容。作者生活在普通法传统下,倾向于在原始法研究中推广案例方法的应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现实主义法学运动。作者深受美国著名法学家卡尔·卢埃林的影响,而后者是二十世纪中叶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现实主义法学运动主张研究实际运作中的法,不要局限于法律汇编里的条文规范,进而认识影响司法活动的各种实际因素,尤其是法官的习惯、活动、作用和所受影响。而案例研究方法恰恰十分重视实际行动中的法,重视纠纷解决的过程和各方参与者的作用,重视法发挥规范作用的生活基础和文化背景。
(3)《切依因纳人的习俗》的经历和成功。作者曾与卢埃林合作从事田野工作,并合著《切依因纳人的习俗》一书。在该书中,两位作者首次倡导在原始法研究中运用案例方法,并身体力行,以充分的案例材料支持自己的研究发现,深受好评,取得巨大的成功。由此,作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初民的法律》中继续贯彻这一方法,自然是驾轻就熟了。
笔者以为,案例研究方法尽管确有过人之处,但也并非完美无瑕,似有以下几处局限:
第一,无法检验作者总结的前提原理。案例方法的逻辑基础是由归纳至检验,即先从特殊到一般,再将一般结论置于特殊案例的检验之下。但是作者从事的归纳和检验所利用的是同一批案例材料,其实是只有归纳过程而没有检验过程。只有获得新的案例材料,真正的检验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有效检验作者所归纳的前提原理及其实现机制。
第二,本书第二部分各章的写作结构不一致。案例研究方法要求,每章须先列举若干项前提原理,然后再结合具体的案例阐释法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机制。第五至八章基本上遵循了这个写作结构。但是第九章的写作结构却颠倒了,先讲法的具体内容,直至章末才姗姗提出十来项前提原理。这个现象说明,检验与否并不重要;或者说,在本书中,归纳与检验事实上只是一个同一过程,而不是相互独立、彼此衔接、互相印证的两个阶段。
第三,归纳前提原理的方法有待改进。问题之一是重要规范上升为前提原理的标准不明确。在本书所研究的几种原始法中,有的以宗教观念或巫术的重要性为前提原理,有的以基本生活物资为前提原理(例如,伊富高人:稻米是一种好食品,页115),各自的前提原理系统所包含的内容差异较大。而作者并未就前提原理的提炼标准作出说明。假如对各个原始法前提原理的提炼标准不一致,各自所归纳的前提原理相互之间就会缺乏可比性,从而令比较研究丧失基础。
问题之二是在特定的原始法中,若干项前提原理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在某一原始法中,作者归纳的十来项前提原理是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如果是,其内在结构如何?各项前提原理之间是否有上位、下位之分,还是简单的平行并列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作者都没有涉及。笔者的体会是,在每种原始法中,前提原理之间的关系显得较为杂乱,十来项前提原理看似罗列堆砌的结果。
第四,案例研究方法的实施难度较大,对民族志研究的要求较高。人类学家从事田野工作过程中,收集案例的实际困难很多。除非民族志研究可以提供足够多的翔实的案例,案例研究方法的优势无法体现;甚至不宜运用这种方法,如果现有合格的案例少得可怜。以本书为例,对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的研究中,案例较为丰富,运用这种方法比较成功;相反,对伊富高人、特罗布里恩德岛人和阿散蒂人的研究中,案例有限,案例方法的运用只好相应地萎缩,让位于描述研究方法。可见,案例研究方法的实施条件较为苛刻,严重依赖现有民族志的风格、方法和水平。
总之,本书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的总体水平不如《切因依纳人的习俗》。这说明,案例研究方法更适合于具体的民族志研究,而不太适于比较研究。
(三)关于基本法律概念
尽管作者十分推崇霍菲尔德关于基本法律概念的理论,并全面运用于本书的研究和表述,其他法人类学家对于这一理论在原始法研究中的应用,却抱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态度:
哈佛大学法学院赛丽·摩尔教授(Sally Falk Moore)明确反对人类学研究采用霍菲尔德的那套术语体系,理由有三:第一,该理论过于简陋(clumsy);第二,该理论人为地将所有法律关系抽象、还原为若干组基本关系,这很可能是一个歪曲法律关系真实内容的过程;第三,该理论将具体的法律关系分解为基本法律概念来认识,会导致人们无法认识法律关系原有的全貌。接着,她建议,“法人类学家可以读一读霍菲尔德的东西,但不要去用它”。[11]
摩尔教授建议在阐述原始文化时使用“中性术语”(neutral term)。例如“合同”(contract)过于专业化,依赖于普通法背景,不宜用于描述原始法的相关内容,而应当用“双方同意”、“有约束力的协议”(binding agreement)等中性术语代替。又如“权利”(right)一词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可以用“利益”(interest)来替换。[12]现代比较法(comparative law)是通过比较研究各个法律体系的相关机制,寻求法律问题解决方案的学科,也面临各个法律体系之间的术语壁垒和文化差异。越来越多的比较法学家逐渐达成共识,要用一些含义相对模糊、包容性强的范畴来构建比较法研究的术语体系。[13]而这些范畴与摩尔教授所说的“中性术语”十分接近。法人类学家和比较法学家在此可谓是不谋而合了。
维尔海姆·奥伯特先生(Vilhelm Aubert)谈到霍菲尔德理论在《初民的法律》中的应用时,倒没有明确否定这种做法;但他认为,如果研究者使用社会学的术语去分析霍贝尔先生的作品,将会更有收获。著名法人类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拉·纳达尔教授(Laura Nader)赞同这一看法。[14]
法人类学研究(原始法研究)采用何种术语体系为宜,一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集中表现为“格拉克曼——波哈南之争”(Gluckman——Bohannan),双方均有精彩论文问世,并吸引众多学者参与讨论。格拉克曼先生主张使用加解释的普通法术语来描述原始法,以照顾英语读者的阅读需要。他曾在关于赞比亚巴罗册人(Barotse)司法活动研究的著作里,借用普通法上“通情达理之人”(reasonable man)这一术语。[15]波哈南先生强烈反对格拉克曼先生的做法,基于他对尼日利亚梯夫人(Tiv)原始法的研究著述,主张应尽量使用当地的本土术语(或本土称谓),依照其音节拼成专有名词,并详细解释其含义。[16](例如特罗布里恩德岛上村庄之间发生纠纷,往往会通过“布内贴拉乌罗”加以解决;“布内贴拉乌罗”指的是一种村庄之间的交换食品竞赛。)
由此可见,为研究原始法确立一种最好的理论工具或术语体系,一直是法人类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初民的法律》引进霍菲尔德的基本法律概念理论,构成其中的一份重要努力,无论如何,有其启发性的意义。
笔者对霍菲尔德的理论知之甚少,仅有以下若干粗浅体会,供批评:
第一,本书中,霍菲尔德的基本法律概念显得并不重要,对分析原始法问题帮助不大;没有这一套基本法律概念,或忽略它们,似乎并不影响阅读的质量和认识的深度。
第二,本书采用的基本法律概念理论,还不是纯粹的霍菲尔德理论,而是经过法学家马克斯·雷丁重述、简化后的基本法律概念理论。(页50)
第三,霍菲尔德理论自诞生以来,在法理学界倒是备受瞩目,争论不断,既有佩服之至者,又有将其贬得一文不名者,一直难有定论。然而,即使在美国,法律实务界却很少受到它的影响。而在我国,它的影响更加微弱。
四、结语
笔者以为,假如要评选“法人类学阶梯”,霍贝尔先生的《初民的法律》一书当之无愧。它尤其适合作为法人类学的入门读物,因为:
一,它较为全面地涉及了法的本质、功用、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有益于加深读者对法的理论认识;
二,它详细介绍了原始法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案例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技巧以及有用的术语体系,有助于读者把握法人类学的科学品质,而且这一整套方法论的意义其实并不限于原始法研究领域;
三,它精选出一批优秀的民族志素材加以介绍,以特色鲜明的文化现象和案例激起读者的兴趣,引导读者对法人类学的感性体验;
四,它在书后附有一份详尽的参考文献目录,为有志于钻研法人类学的读者打开了一座精品文献宝库,同时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学术积累,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笔者对此书所作的批评,难免有吹毛求疵的地方,然而这并不减少笔者对此书的喜爱以及对作者深深的敬意!
【注释】
[1]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and Law-ways of the Comanche Indians.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Memoir No.54,1940. See Laura Nader,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ublished in 1969, reprinted in 1997, p.426.
[2] The Cheyenne Way,with Karl Llewellyn.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41. See Laura Nader,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429.
[3]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s as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Primitive Law. Yale Law Journal 51(6) 951-966,1942. See Laura Nader,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426.
[4] With A.A.Schiller, he also translated from the Dutch and edited Haar’s Adat Law in Indonesia. See Laura Nader,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441.
[5] 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法的动态比较研究》,周勇译,罗致平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封二。以下凡引用此书内容的地方,均直接标出页数,而不再另行起注。例如,“法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当它被忽视或违反时,享有社会公认的特许权的个人或团体,通常会对违反者威胁使用或事实上使用人身的强制。”(页.30)
[6] See Thomas R. O'Connor, Laws on Crime, < http://faculty.ncwc.edu/toconnor/111/111lect04.htm>, Jun.10, 2003.
Here's a couple definitions of law by a famous anthropologist and famous sociologist:
"A law or legal norm exists if its neglect or infraction is regularly met, in threat or in fact, by the application of physical force by an individual or group possessing the socially recognized privilege of so acting." E. Adamson Hoebel (1954). The Law of Primitive Man. NY: Antheneum, p. 28.
"Law, legal rules, and order exist if they are externally guaranteed by the probability of coercion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to bring about conformity or avenge violation, and is applied by a staff of people holding themselves specially ready for that purpose." Max Weber (in Max Rheinstein, 1954, Max Weber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p. 5.
[7] See William Nixon, Legal Anthropology, , Jun.10, 2003.
[8] See William Nixon, Legal Anthropology, < http://www.indiana.edu/~wanthro/legal.htm>, Jun.10, 2003.
[9] 严存生:“译者前言”,见E. 霍贝尔:《原始人的法》,严存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10] 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50。
[11] Sally Falk Moore,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Studies(PART.Ⅳ), see Laura Nader,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343.
[12] Sally Falk Moore,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Studies(PART.Ⅳ), see Laura Nader,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342--343.
[13] See Konrad Zweigert & Hein Koetz,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 translated by Tony Weir, third revised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 p.44--46. “A system of comparative law will thus seem to be rather a loose structure. The component concepts cast a wider net than those of national systems.”(p.45)
[14] See Laura Nader, Introduction,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3--4.
[15] See Max Gluckman, Concept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ribal Law, see Laura Nader,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349--373.
[16] See Paul Bohannan, Ethnograghy and Comparison in Legal Anthropology, see Laura Nader, Law in Culture and Society, p.401--418.
本文摘自《法律书评》(第2辑)。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