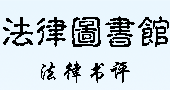法治社会的自治:一种外在视角《法治的生态环境》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张健 2006-11-23 10:27:16
姚建宗老师的又一本专著《法治的生态环境》(以下简称《法治》)出版,这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与目前国内许多法理学著作一样,《法治》同样把国家和个人常常谈论的“法治”一词作为自己问题的论域,只不过在这一问题进入视角上选取“生态环境”进入和展开。《法治》(自序)标题提示,这是“一个法律‘边缘人’对法治的思考”,在法学学者更多地从专业的角度考虑,从立法、法律程序等进入“法治”思考的今天,或许作者早已意识到,书的题目是很容易被专业化的学者边缘化而提不起他们的阅读兴趣。对于自己可能被法学界和法学理论边缘化认识的原因,正像《法治》(自序)表明的那样,作者认为“这种感觉来自于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我对我国法学和法学理论的现状尤其是它的毫无‘立场’极其失望和不满,因而我的科研活动与科研成果表达了对这种状况太多的批评。”因此,一个很“土”的问题,又很边缘化地思考,决定了《法治》向人们展现的是一个棘手问题。所以,这也是作者选择了“生态环境”这种“向窗外看”的外在视角进入和展开,而不是选择“向窗内看”的内在视角,即以纯法律问题(如立法、法律程序等)作为问题进入的原因。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这两种法律研究方式都不排除对法律的深度透视,只是选取的视角不同,但是“向窗内看”的内在视角的缺陷在于,一、采用“局内人”看局内问题的方法。制定规则是在当下几个人做出的意在减轻负担而做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在以后成为其他人的游戏规则,实践规则的实践者本身并不制定规则,只是有限地影响着规则的制定。二、注重法律体系本身的形塑并使法律有实体化倾向。三、由以上两点产生的结果是,法律封闭地存在着既不能产生来自外部的批评,也不能产生来自内部的批评。不能产生来自外部的批评源于自身的封闭,而不能产生来自内部的批评是因为法律自身反思能力的减退和失去。四、这种内在视角容易产生法律的实用主义和拿来主义,并忽视当下所生活的社会生态和真实人的存在状态。法律实用主义不能对法律整体可能产生的秩序给予横向和纵向的观照,即忽视法律、经济及社会的可能联系,并且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而存在,这种法律实用主义把社会发展之间的复
杂联系用法律公式化和简单化。法律实用主义的极致是法律的单边倾向,即把法律视为某一方面的问题,用“法律背后的故事”代替“法律是什么”。
“法律背后的故事”与“法律是什么”这两个命题是有区别的,例如,一个普通人在是否涉讼前后表现会有所不同,在涉讼之前他会以一个普通观众的心态(同意某一判决,或批评这一判决)对待任何严肃的案件,而保持一种轻松的心态,作为普通观众可能是满足好奇心(或源于好学,或源于猎奇),即他(她)更关心“法律背后的故事”。这种关心“法律背后的故事”的好奇心仍然不是站在法学的立场上思考“法律是什么”;也不是在涉讼之后更关心会受到怎样审判结果。因为在涉讼之后更关心来自“法律是什么”方面的法律解释和学理解释而不仅仅是好奇心。法律人和法学家作为法学局内人而不是普通观众和消费者,他(她)们从事的是“法律是什么”的工作和事业,这种工作和事业作为社会角色的工作有别于人们私下的闲谈,法学界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也更多卷入了媒体这样吸引眼球的工作,并用“法律背后的故事”代替“法律是什么”,这种现象表现在,一、传媒上经常出现法学家和娱乐明星一样成为案件的侦探,更多地把观众故意带入案件的玄妙之中(并且其意仅仅为此),而不是更多地指出其中的法律问题。这些法学家没有揭示法律的复杂性,普法的目的也是有限的,而仅仅提高了传媒的收视率。二.用历史上某一时期、某一环境下发生的事件解释当前环境下的“法律是什么”,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法律是什么”存有不同。法律是历史长河的跳动之波,正义是这一长河的涌动之源。法律的存在离不开作为背景的价值、利益和目的,从而使“法律是什么”表现出代际性。三、这种做法不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当下的中国社会,把历史上或刚刚过去的偶然的甚至欠真实的事件作为“法律是什么”。这种实具新奇的“法律背后的故事”并不完全符合法律实践和经验,而仅仅是法律故事之一,并且任何故事的发生都有偶然性和非常态性,所以法律故事的偶然性不能代替法律的抽象化、形式化、稳定性。既使我无力否认法律人和法学家对中国法学和法制进程的推进,但上述现象仍部分地存在,许多案件是实实地发生的,但是在对待案件的态度上已经致使案件本身无力被解决了。
《法治》对生态环境的定义是这样,“实际上,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东西都肯定地是有一个作为其基础并与其相调适的生存背景或者生存环境――也就是其‘生态环境’的,因此,它们都是极其复杂的而决不是简单的。”[1]
《法治》不是在告诉人们应该选择什么样规则的“唯立法论”和“唯物(制度)论”,而是认为“由上述思维倾向所制约,我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对法治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所展现的单一视角和单向维度,便不能不表现为既与我国的法治理想相疏离又与我国法治的现实相脱节,其真实的价值与意义也就不能不存疑。”(页1-2)作者选取了“生活立场”、“生存土壤”、“制度基调”、“人文情怀”、“时空场域”、“意义的现实载体”、“法律环境”作为“生态环境”认识上的视界和维度,把法治放在宏大的场景之中,《法治》在理论展开平面上梳理出这几个似乎并不相关的维度,正像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在“‘复杂’地看‘复杂’的法治”。与单一视角和单向维度的本体论思维不同,《法治》采取了认识论思维表达了对法治的看法,认识论思维方式一般采取批判的立场看待周围的世界,相对于所批判的对象来说,批判者持一种“外在观点”。哈特根据人们对法律规则的不同看法,划分出内在观点和外在观点两种对法律规则的划分,“一种是内在观点(internal point of view),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指他接受这种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的人。另一种是外在观点(external point of view),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指他本人并未接受,但却是观察这些规则的人。”[2]法律规则上的“外在观点”是从法治方面的外在视角得出的,“外在观点”是一种观点和结果,而外在视角是一种方法。“内在观点”与内在视角同理亦然。法治的外在视角更多地考虑人的因素,不是强制性地使人服从法治之内的各种规则,而是在实现法律治理之前使人做好准备,即面对设想实现法治的我们自身比想欲实现的理想中的法治更不成熟的事实,强调外在因素和人的成熟的重要性,而只有人的成熟才能给死的法律以活力。简单地接受或拒绝一种理想中的法治的内在视角很容易忽视在走向法治之路上,人的因素以及人的环境因素对人的精神的塑造。《法治》对“法治的公共话语语境”的论述充满了激情,“所以,分析探讨法治实践所面对的社会公共话语及其所蕴含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情感、社会道德观念与社会价值准则、社会认知与社会思维方式,对于法治实践本身具有重大意义。”(页248)这种重大意义的获得是以参与主体的形成为前提,即要认识到“我”是谁和怎么样,也要认识到“别人”是谁和怎么样,以主体的启蒙意识的获得和社会的某种行动自觉为依归。同时,在法治理想实现方式和过程方面,《法治》深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但《法治》更多地是从中国的国情这种生态环境的状态及其演进出发,而不是从哈耶克思想形成的脉络出发,接受了哈耶克的结论而不是其理论产生的过程和条件,即更多地考虑法治问题作为一个老的本土问题在当下环境中如何生长。《法治》“更倾向于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
二
姚建宗老师多年前曾进行法律与发展方面的研究,这对任何法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这一难题在于作为一种当下的法律与发展研究离不开发展的历史过程,也离不开发展本身的研究,并且因为发展本身的不确定性和难以把握性,加大了法律与发展横向研究的难度,从法律的视角透视法律与发展研究的相互关系正缺少这一平台发展这一理论。法学研究者历来喜欢从内在视角出发的研究方法,而不太关心外界其它社科研究的发展情况,因此法律与发展的研究更少受到重视。姚建宗老师或许意识到法律与发展研究问题的艰巨性,因而把其研究成果成书为《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以下简称《导论》)。该书给我们带来了两个信息,一、发展问题独立于法理学问题而存在,法律与发展研究主要限定在理论探讨的层面,基本上是一种法理学研究。[3]二、因为作者认为该书只是导论性的,因而给那些对于法律与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同仁以期待。但是,多年来,姚建宗老师没有对法律与发展问题进行理论深入并对导论进行展开,我们并不知道他对这一问题有怎样的考虑或有哪些看法的变化,与此同时,法律与发展问题与多年前相比,在中国的生态环境下已经成为紧迫的问题。但是通过对前后两书的比较可知,《法治》中的问题并不是《导论》中所列问题的横向延伸,而是更重视现实性问题的纵向展开,如《导论》所言的“法治理想”变成“法治现实”的问题。[4]从方法上讲,《导论》仍然给《法治》留下了用发展的眼光看法治问题的视角,即《法治》中一再强调的复杂性的发展问题,但是,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与发展问题仍然是两个范畴的问题,发展问题作为具体问题的汇合并不具有方法上的普适性,而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例如,中国耕地面种逐年减少、土地荒漠化中的发展问题,与理论方法上怎样发展一种理论而不单单是建构一种理论是两回事。《法治》与《导论》的差异之处在于,一、《法治》不是像《导论》那样对问题的占有,而是对具体问题的深挖和展开,权利(主要指个人权利)仍然是《法治》一书中实现法治的描述和分析基点,“所以,对于法治而言,国家优位观念当然不足取,但社会优位观念也同样有其缺陷与矛盾,只有个人优位观念才是其根本,也只有个人优位观念基础上的社会优位观念才能与法治相容。”(页5)《法治》的理论展开也是以这一问题而寻找路径、土壤和载体的。二、揭示法治理想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既体现在生态环境上,也体现在作为生活立场之理想的实施过程当中。三、《法治》对制度基调的设置不是放在如何实现理想之善的多样性上,而是放在理想实现时可能受到的限制上。《法治》采用了悲观主义基调的内敛式法治设置。(页125)四、信仰法律并遵守良好的法治启蒙是法治所必需的,致此实现人权和人的发展。
笔者认为,《法治》对法治问题并没有采取建构的方式,更多关心实现法治时所需要素的分析上,即分析各个要素与理想的法治要求之间有着何种关系,如果《法治》与《导论》中“法律与发展研究”有关,那么这种相关性也体现在关注人的发展上,是“法律与发展研究”的浓缩,把眼光放在了不断移动的人身上。《法治》不同于多数国内学者对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区分及其各自的操作路径,(页9-10)即不同于形式法治也不同于实质法治。《法治》的论述更倾向于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创造条件,不是从某一社会群体或社会现象在特殊群体的内在视角出发的,而是从外在视角来分析的。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通过简单化或复杂化处理就可以解决其中抽象着或隐喻着的问题,使问题变得容易处理的最大可能是处理问题的人。《法治》正是为了寻找这样处理法治问题的人,并对怎样获得这种理想的法治中人作出设想。姚建宗老师用“产床”这样的词来形容生态环境,这种拥抱法治的热情正在激发一个学者的想像力,但是在各章之间论题相关性方面因为没有进一步的逻辑说明和深挖,而对读者有一种突兀的感觉。
三
《法治》对法治这样定义,“我们认为,所谓法治,简而言之就是合法权力在充分尊重社会习俗和历史传统的前提下,运用合法程序制定的反映社会生活真实运作规律的良法而对人类行为及其生活的规制与调整,以及这种规制与调整的过程与状态。”(页114)法治包含着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作为体制外的社会习俗和历史传统是体制内的良法的源泉性支撑。“尊重社会习俗和历史传统”本身就是尊重社会的自治,而实际情况是社会自治不是法治,一些没有实行法治的社会也可能实现自治,如主要由血缘和情感编织的家庭中的关系并不是由法治支撑,但却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治;而社会中的法律至上也不是法治社会的自治。《法治》把法律的至上性和法的人格养成看作是法治的共同要素,即法律的至上性和法治社会的自治共同组成法治,法治不仅仅包括创建法律方面,而且包括法律实现方面。法律至上处于法治目标创建和实现过程之中,包括立法、司法等组成的法律体系运作的权威性,法治社会的自治主要是法治社会的公民实现法治启蒙的过程。法律至上和法治社会的自治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理想中的法治社会。不管是主张法治是由下而上地自发形成,还是由上而下地人为建构,都离不开在地上行走着的人的真实的活动,提倡法治时主张法律的至上性时正是因为有了人的参与,法治才时常脱离它应然的轨道而演变为人治或治人。人治是人高于法,人驾驭法,而不是法框定和制约着人;治人是人治社会的一个方面,即法律变成了目的性很强的东西,不是着眼于法治之公共利益,而成为实现私人利益的工具。如果作为具有批判性的法学和法律在人的参与和实践面前的失语和批判力的丧失,那么,既使表面上法律在这种失语和批判力丧失的社会中存在着,法律在其中的运行也不是真正的法治,原因在于我们最想实现的法治和正在运行的所谓“法治”并没有真正实现自治,而被某种力量牵着鼻子走。法治社会的自治并不是法治之路走向自我封闭,恰恰相反,而是法治从单纯的理性建构的道路上走出来,反向求诸于日常生活,作为主体的公民从心理、智识上拥抱法治、喜欢法治、理解法治、实践法治,使这种人们意欲实现的法治在实践的层面不致于成为于己无关的东西,而是一种理性的参与,不至于使公民在法治面前沦为无意识的“赶集”,这种无意识的“赶集”会使人们理想中的法治成为幻灭人们理想的东西。一句话,实现法治首先需要能够在法治社会中实现自治的公民的大量出现。《法治》认为这样的自治公民应该“具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平等独立的人格”、“相互平等地尊重的基础上更容易彼此宽容”、“在相互交往、彼此共同活动的领域,更易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在发生各种矛盾、纠纷或者冲突的时候,往往更多容易妥协”、“在自治的生活和行动中更有责任意识”、“具有公民的美德或者风范”。(页57-58)《法治》对法治社会自治公民的品性和特质的规定并无令人耳目一新之处,而正是这些人们常常提起的人的基本素质却是人们在面对法治时常常遗忘的。《法治》不同之处在公民的品性与特质的获得方面所作的努力走得更远,而这种常常提起又常常遗忘的人的基本素质作为公民社会自治一部分,更容易被看作私人性的东西,其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和个人观点也会被人看作(如本书作者所说)“边缘人”的。这种误识在于《法治》的目的可能不在于提出更多的理论问题,而是在于提醒人们走入法治殿堂之前的精神历炼,以及侧重人的因素方面的法治实践的可操作性。
在《法治》的理论进路上,作者首先选取的不是法学界熟识的法学进路,而是一种从法学之外的视野进入法学的进路,论述中引入了哲学、美学、心理学的某种观点为该书的论证作铺垫,加之该书视角的多层维度促使全书有一种极强的理论弹性,这种理论弹性最终归结于“法治的精神意蕴”的获得。在“法治的生活立场”一章中作者提到了信仰问题,“法治的意蕴便是人对法的神圣性的制度信仰”。(页29)而这一提法与几年前提出的“信仰:法治精神意蕴”一文相呼应,表明作者多年来理论态度的一致性和观点的相似性。而余下几章也主要着眼于制度前的铺垫,强调人的信仰问题和精神性因素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如果缺乏学术研究的批判和反思,学术观点也会流于宗教式的陈述,《法治》从其所生活的当下环境入手,使信仰问题和精神性因素与生活的逻辑相互渗透,即避免了口号化倾向,也躲避了宗教化倾向。法治需要某种“制度信仰”,这种“制度信仰”与宗教化倾向有所不同,宗教化倾向表现在信仰的非理性上,即不关心所信对象如何,而信其应该如此。法治信仰问题是一种理性行为而不是非理性行为,法治信仰具有地方性和本土性,是信仰者理性选择的结果,即法治的信仰是培养出来的而不应该在强制下产生出来的,宗教化倾向有渲染和神化的成分,这与作为理性制度安排的法治是相悖的。有学者认为启蒙与信仰是矛盾的,[5]但是毕竟启蒙式地有所信仰与信仰式地有所启蒙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先有启蒙后有信仰存在,而后者是先有存在的信仰后有启蒙。启蒙式地有所信仰和信仰式地有所启蒙是有区别的,比如我们教育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信仰某种宗教和教育她(他)们养成某种信仰是不同的。对于法治问题,《法治》一书认识到启蒙先于信仰存在的重要性,由于这种区分在《法治》中不太突出而容易使人误解。
法治社会的自治是用一种外在视角认识尚在研究中的“法治”。现在,对法治社会的认识存在一个误区,过多地把“法治”理解为“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较少考虑这种“有法可依”当时所立之法在生态环境里是否能够生根并成长,即是否能够把法在人们的心中树立起来,成为值得膜拜的封碑和指示性的座标,一旦这种在当下的生态环境里并不能生根的所立之法被执行起来可能错误不断。这种“有法可依”式的思维本身并不存在可非议之处,问题在于“有法可依”式的思维作为内在视角仅仅是在实现法治社会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这种内在视角并没有反思所立之法是否是法治社会所需之法,是否是所知之法,是否可接受之法。而根据这种“有法可依”式思维推导出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自然理解成法治社会中“法治”的全部,作为法治社会重要载体的权利运行有被扭曲之虞。因此,只重视权利在法条上的规定,忽视权利在入法之前的生成;只重视权利的普遍性特征,忽视了在现实生活中弱者的权利更容易受侵犯;只重视权利体现在法治社会公民身上的一点一滴和一个部分,忽视了每个人的权利更好地组成之后能够给权利成长的土壤带来一片绿色。
法治社会认识上的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的区别在于,前者重视立法中法条的生成和执行,而后者更重视立法之前“观念先行”、“精神意识之培育优先”。托克维尔曾经提出,“我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我觉得应当把它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做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6]托克维尔看到了民情对法治的支撑,民情是一种先在的独立状态,所以在看待法律时要考虑到法律与民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托克维尔论述,“于是,我想像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把法律视为自己的创造,他们爱护法律,并毫无怨言地服从法律;人们尊重政府的权威是因为必要,而不是因为它神圣;人们对国家首长的爱戴虽然不够热烈,但出自有理有节的真实情感。”[7]托克维尔在特定的地域内经验地看民情,而不是科学地看民情,不是把法律看作是某些人强烈要求的结果,而是看作一种民情推动的结果,法律作为民情发展的必然,成为实现法治的一种自然引入机制,法律是民情的升华。而《法治》正是在法治的道路上揭示这种自然引入机制的存在,并论述这种自然引入机制如何能形成。所以,《法治》所说的“复杂性”并不是法治作为一种机制本身有多么复杂,而是认识到这种在某些方面有些成熟的法治(包括理论上和操作上),在具体的生态环境下产生了复杂性。
边沁认为,“法律是什么,在不同的国家中有差别而且差别很大。然而,法律应该是什么,在所有的国家中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8]《法治》不是采用内在视角的解释者的角度来看待法治,而是对法治建设采取批判的立场,这种批判构成了实现法治的前奏之一部分。所以,在各自寻找和确证“法律是什么”的道路上,对个人和一种制度有意义的是,不是简单地提出许多学说,也不是简单地对各种职业和功能进行不断划分,而是对作为背景的生态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种作为背景的生态环境是这样存在的,即怎样形成由满眼草地形成绿意意义上的,而不是向沙漠中寻找绿洲意义上的,前者意在消灭沙漠而后者不是。在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上,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中国队和世界第一的巴西队同组,中国队输了,中国足球界没人提出如果踢352或451阵型,中国队就会战胜巴西队,因为,我们承认中国足球不如巴西足球,中国队输给巴西队不是输在排兵布阵上,而是输在足球整体的资源上。整体资源作为一种背景,其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足球与法治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由各自的生态环境决定的,足球先进与否不是由这个国家习惯的踢法决定的,关于决定“法律是什么”的评论和法治是否成立的争论,不全是由是否立法、立什么法决定的,而是应该清楚什么样的法对我们更合适。所以,应该对法治与立法划等号的作法保持谨慎的批评。
联邦党人在美国建国前论述了精神准备的必要性,经过周密的考虑,完备的宪法是需要的,“但是,所有各方都会承认,我们的宪法并不是什么抽象理论的产物,而是‘我们政治形势特点所不可或缺的互相尊重忍让、友好敦睦精神’的产物,既然如此,从理论上去考察这部宪法的任何部分,也就是多余无用的。”[9]法律是需要的产物,法律也需要去信仰和爱戴,作为某种精神的体现,法律不是僵化的。法律之中的诚信不仅体现在合同双方之间,也体现在合同双方之外,因此在违背诚信时应该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也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这种社会压力不仅仅来自某些具有高尚道德的某种良心,也来自社会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出谴责。
法治的生态环境复杂性展开是实现法治的难点,作为阶段性成果的标志,《法治》尚没有对法治生成所需的必要条件进行有机地要素区分以示同仁。法治的信仰和法治的精神最终要回到法治的运行,从法治的运行中获得法治的信仰和法治的精神不是仍有可能性吗?在一个所具有的信仰不能运行的社会,难免其精英化和个性化理论大于其社会化理论实现,虽然《法治》作者对法治的信仰是坚定和连贯的。理论的推进对于单兵作战学者来说是困难的,因为社会科学理论本身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使理论主张不得不返身求助于前人所积累的成果。而在当下对法治理论的研究,学者们的单兵作战很难产生一蹴而就的效果,甚至对前人作为整体的理论人为切割,或许姚建宗老师也在为此困惑。理论的推进不同于理论的推动,理论的推动不同于理论的骚动。事实上,带着理论推进的初衷,更多的理论并没有获得前进,而仅仅是在动一动的情况下复归原位,而更多的是,在推动中有更多骚动的因子,而这种理论骚动更多产生于理论信仰和理论精神的缺乏,而《法治》作者对理论信仰和理论精神的坚持是一贯的,《法治》作者用这种一贯的坚持时刻会对人有所促动,然而作为理论推进的目标并非一触而蹴,走上法治路途尚十分艰巨。理论的推进是每一个研究者的任务(当然包括学理的批评),为了避免走入理论骚动的误区,《法治》中对法治生态环境的纵深推进是横在这一理论面前的门槛。
(姚建宗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1]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页15,下文引自该书的仅在括号内标注页码。
[2]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页191。
[3]姚建宗:《法律与发展研究导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页15。
[4]同上揭,页417;
[5]朱苏力:《面向中国的法学》,资料来源:(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信息网,最后访问时间:2004年5月20日。
[6]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358。
[7]同上揭,页11;
[8]边沁:《政治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4月第1版,页97。
[9]汉密尔顿等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页314。
本文摘自《法律书评》(第3辑)。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