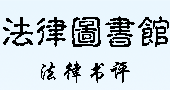权威、规则与宪政《政治与市场》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陈国申 2006-11-20 9:53:18
事实上,对于权威、规则与宪政的论述在林德布洛姆的大作《政治与市场》里所占比重很小,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能掩盖它的光彩。林德布洛姆正是在完成了对“权威、规则与宪政”论述的基础上才提出了他的大众化控制理论,也即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是他多元政制理论的基石。权威是他整个理论大厦中的一个核心要素。《政治与市场》是林德布洛姆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对比分析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制度中比较具体代表意义的几个类型,抽取出了被他称之为政府与市场理论分析的三个核心要素:权威、交换和说服。其中,权威又是核心中的核心。他指出,“政府以权威为基础”,“权威是使政府成为可能的核心现象”[1]在林德布洛姆看来,政治在本质上就是“为着权威的斗争”,“在一个被叫作政治的凌乱过程中,想要权威的人为它而争斗,另一些人则试图控制掌握权威的人。”[2]权威之所以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对象,是因为权威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方法,这种控制方法的实施非常简单,“有的时候甚至一个字也不需要,在权威关系中,一个驯服的人懂得,需要他干什么,不需要他干什么。”[3]在一个权威网络里面,普通人要服从于官员,不同职能的官员相互服从。尤其是政府权威,“它拥有对其他一切人或权利要求的权威,不会遇到来自于一个与之平起平坐的权利要求者的挑战,它在维护自身秩序方面具备居于其他一切组织之上的权威。在冲突的情况下它也许无法使其声称的优先权生效;在某些场合它甚至可能无法谋求实行优先权。但是它对优先权具有的要求的普遍性和唯一性,使它与众不同。”[4]
尽管权威在一个社会里面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在任何社会里,权威都不是绝对的。无论斗争如何进行,它总要使权威处于某种程度的控制之下,权威从未彻底实现过单向度的控制。不管斗争者是以所谓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的身分出现,即便是斗争者取得了权威斗争的胜利,最高权威仍然会受到至少是微弱的控制。由于控制国家的巨大价值,它必然会激起无穷无尽的斗争,只要有斗争的存在,争取斗争胜利的所有竞争者都必然要寻求支援。后援组织对争取权威的斗争者来说太重要的:
虽然政府的最高权威可以使用政策和军队来强迫从官僚制和人民那里获得权威的授予,它却不能够在后援组织内这么做——除非它可以在这个组织中创造一个有能力强制多数成员的比较小的集团。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给这个较小集团的成员们提供好处,以求得他们对权威的认可。从特定角度讲,在每一个制度中,最高权威最终不可避免地要依靠一个后援组织,这个组织建立在多种交换和说服、而不是单向度权威的基础上。[5]
能够对权威实施控制的后援组织各类非常多,比如利益集团、军队或者其他组织。事实上,后援组织对权威的控制众多控制方式中的一种。但在林德布洛姆看来,诸如此类的种种相互控制却从未建立过足够的民主控制的可能性。那么什么是林氏理想的控制方式?
林德布洛姆认为,最高权威受着规则的约束。“那些参与控制最高权威的人――顾问委员会、集会、选举团成员――根据规则控制最高权威。”[6]这些约束性规则既有制订成法律的,也有未制订成为法律的规则,比如在最高权威内部,有些规则看来主要是心照不宣的协议,有些则代表着小小的正式组织的成员们之间的明确协定:
处理争夺权威的斗争的规则有时来源于明确的协定和缄默的理解;这种协定和理解约束了争斗的残暴性。当人们为国家机器的权威这类巨大的价值而争夺时,他们必然会担心可能遭受穷困潦倒、被关入狱、肢体残缺或遭到杀戮,假如自己失败的话。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们通过在减少他们的风险的规则上达成协议,试图软化这种争斗。失败者会受到体面的对待;他们保有的不止是他们的兵权,还有他们的自由和财产。今天,对于生化武器、毒品和原子武器的使用的害怕心理,也约束了各个国家。无论如何,迄今为止就各种规则对暴力和强权的约束而言,它们保护的不光是权威的争夺者,也包括整个人民。[7]
在林德布洛姆的眼里,这种对争夺权威斗争的限制规则,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巨大进步。
在比较短的时段内,这种进步意义体现的不会太明显,但如果我们把观察的视野拉长,这种进步意义就会更为明显。
人类产生之前的权威斗争规则我们无从考证,只好借助于其他灵长目动物的竞争机制。非人类的灵长目动物的研究专家证实,所有已知的此类动物都是群居的,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它决定着群体中如何分配有限的食物和如何形成配偶关系等。当群体中掌握最高权力的“首领”突然死亡时,经常会导致群体的分裂,因为这时群体内部往往会发生激烈的争斗,以抢夺暂时空缺的“首领”职位。[8]数日前《北京青年报》连载的“猴山政变”所引起的流血冲突,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灵长目动物的权力斗争方式是最野蛮的,此时没有任何规则。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在土著社会*,主要有两种继承方式:泛布性领导和世袭继承。[9]群队和部落社会属于泛布性领导阶段,权力继承非常简单,没有继承:随着领导人的去世,他的权力也就消失了,任何竞争者都必须重建自己的实力基础。此时权力是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是无法转让。在酋邦和早期国家中,权力继承的方式主要采取世袭制,乌干达的布干达人就是采取这种继承方式。权力继承首先是法定原则,根据这个规则,国王的所有儿孙都是候选人;其次是优先原则和人格因素,根据这个规则,布干达人选择的权力继承方式是兄弟继承,而非子孙继承,继承的手段是叛乱,这时斗争者的成熟和实力显得特别重要。土著社会的泛布性领导阶段的权力继承方式比较接近于灵长目动物的方式,因为新权威的确立完全依靠个人能力;世袭制阶段的权力继承规则相对明确,但相当大程度上还要借助于武力和流血冲突,也比较野蛮。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权力继承的规则我们都比较熟悉。我国古代长期采用嫡长子继承兼顾竞争原则,以嫡长子继承为主,如果其他皇子通过权力斗争取得胜利则采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在西方,权力继承规则相对我国来说显得比较复杂。在古希腊整个历史期和古罗马的共和制阶段,权力继承以选举为主,个别时期间隔以僭主暴力夺权。随着古罗马的军事扩张,古罗马逐渐进入帝国阶段,权力继承问题从屋大维时期开始了西方历史上最混乱的阶段[10]:皇帝不断改变自己的继承人,比如屋大维在位四十四年中有三十七年一直都在不断更换继承人;皇权旁落时,皇亲贵族还不断阴谋废帝;确定两个以上继承人时,还会经常出现宫廷杀戮。中世纪以来,由于王权较弱且权力继承规则相对明确,以流血冲突方式解决的权力继承问题的现象大大减少了。西方国家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后,权力继承主要依据宪法规则采取民主选举方式来实现,权力继承基本上不再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目前仍徘徊于军事政变与民主选举之间。
总体上说,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权力继承并未完全以文明、和平的方式解决,而是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局面,在规则明确时,权力交接相对容易平稳过渡;规则不明时,权力交接往往以暴力冲突的方式实现,并且随着军队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冲突的规模及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
林德布洛姆进一步指出,规则对权威所确立的约束主要有四种[11],分别是:第一,最基本的约束是那些古老的禁忌,即众所周知的私有财产的权利,禁止别人对权利主体的干预,其中也包括统治者的干预。第二种约束是对未专门规定的广泛权威的削弱。林德布洛姆指出,权威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权限的不明确,最高权威所拥有的权力应仅限于被明确授予的范围,权威只能是特定的――适用于特定环境、特定对象,并且这是人类可以被宣称的最伟大的创造。第三种规则是权力的分离:规则指定某个最高权威在一个位置上,另外的最高权威在另外的位置上。这样便限制了任何一个权威的暴政。第四种规则是监察和平衡。最高权威分离后,规则提供了对权威的进一步限制,给予了每一个官员相对其他官员的权威,便有了权威之间的制衡。
如果说人类在权威斗争方式问题上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对这种斗争给予了规则限制,那么另一个重要进步就是这种规则进一步发展成为法律,那就是确立宪政。
在林德布洛姆眼里,对权威的约束性规则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则,但其中只有一部分制订成为法律。[12]比如谴责暴力行为的伦理规则就是一种普遍规则,禁止杀死政治上失势的领导人就是当政领导人之间的一种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党内多数决定则属于个别正式组织成员之间的明确协定。但这些规则上升为法律规则之前,都有一系列明显缺点,即不稳定、不够明确、缺乏可执行性、普遍约束性较差。如果仅由这样一些规则来约束权威及权威斗争,那么权威的任意性、残酷性和危害性就无法真正有效地得以制约。我们还以权力继承为例来说明问题,比如,我国两千多年的古代专制社会中,我们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并非没有明确的权力继承规则,虽然这个规则本身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足够明确,但这样一个规则的缺陷就是:最高权力掌握在一个懦弱昏庸的人或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手中,对整个社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于是比较精明的皇帝便有时放弃这一名义上的规则,辅之以择优原则,从众皇子中择优确立为太子。但这样一来,长子继承制这一规则本身的权威就大大折扣了。同时又孳生了一系列问题:新太子的合法性微弱,导致其他皇子对太子位置的觊觎,众皇子便拉帮结派,造成内政不稳,稍严重一点便酿成政变甚至战争。因此,对权威的约束规则迫切需要明确化、权威化、稳定化。
对权威的约束规则上升为法律甚至宪法,这便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特征。法治与人治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规则,而在于这个规则是否明确要求所有人都有平等的遵守。“法律也完全可以确定一种以世袭继承为基础的王朝制(a royal government with a hereditary succession),但是它却绝不能选定国王或指定一王室家族;一言以蔽之,任何与特定个人相关的事务,都不属于立法权力的范围。”[13]在法治社会中,法律一旦制定出来,任何人都没有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是否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是否属于立宪政体的标准。
至此,人类对权威控制的线索已经非常清晰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从失控的权威发展到受到规则约束的权威,再从受规则约束的权威发展到受法律约束的权威,即立宪政体下的权威。当然在林德布洛姆看来,这还不够,他又提出了一个对权威的大众化控制。但笔者认为,对最高权威的大众化控制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不过是立宪权威的一个组成部分或阶段而已,因为大众对权威的控制也要服从规则,否则便会出现大众的专制。当然,对于我们目前的政治改制改革而言,《政治与市场》中关于“权威、规则与宪政”这一问题的阐述已经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了,这也是我推崇这个片断的原因。
(林德布洛姆著:《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注释】
[1]林德布洛姆著:《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王逸舟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19、26。
[2] 同上揭,页175。
[3] 同上揭,页20。
[4] 同上揭,页26。
[5] 同上揭,页178。
[6] 同上揭,页185。
[7] 同上揭,页186。
[8] 董建辉:《政治人类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92-93。
* 笔者未用原始社会、初民社会、野蛮社会几个概念,因为这几个概念都带有一种当代人的偏见,认为他们是野蛮、落后和不开化的,这是人类学者所尽力避免的一种倾向。当然我们在宏观上进行权威斗争规则比较研究时,是无法完全摆脱“价值”判断的,但我们还是要尽力要以“他者”的眼光来观察、体会土著社会。
[9] 参见前注8揭,页95-106。
[10] 参见严家其:《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7-40。另参见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
[11]前注1揭,页187-188。
[12] 参见前注1揭,页186。
[13]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页245。
编者注:本文摘自《法律书评》(第2辑)。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