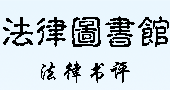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庞正 2006-9-6 13:53:35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随着商品、资本的不断扩张,现代化问题已陆续成为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被动或主动地直面着西方文明的冲击。在这个具有悠久而沉痼的历史传统的文明古国,现代化是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流;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为中华民族能够走上富强昌盛之路而奋斗不息,同时也有众多志士仁人为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挫折而迷惑不已。这 标准是什么?如何消解传统文化?现代性(化)是否等同于西方性(化)?中国现代化的模式及进程如何等等。在“法制现代化”这一特定论域中,前述问题被转换为如下理论向度:现代性(化)的法制是怎样的?如何处置(包括认识)传统法律文化?怎样理解东西方法律文化关系?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应具备怎样的历史样态?相信对该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回答与处理,都将是中国法治化道路上不可推卸的任务。南京师范大学法律系夏锦文教授的《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一书是我所看到的对“中国法制现代化”这一论题作出较为全面、成功的著述之一,它在内容上恰切中肯地回答了“法制现代化”话题所应涵盖的主干问题,在方法论上具有很强的历史感、现实感,并特别注重两者之间的相互观照。本文就该书的一些理论内容与思考路径作一些评介。
一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这一论域中,两方面的思考维度必须被论及: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因为这是设定“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前置。如果将中国法制比作一辆不断前行的大车,那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便是其两个车轮。在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往往会偏废一个轮子而过份倚重另一个轮子,甚至于两个轮子都偏废。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我们对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的认识偏颇有着极大的关系。夏锦文先生在《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一书中对此的处理是极为妥贴而富有启迪意义的。
首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认识,在我国法学界甚至整个思想界都时有见地,并且“这些观点都从特定的角度总结并表述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的主要精神风貌和形式特质,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和法律生活的基本事实。”(见该书第6页)颇具新意的是,夏锦文教授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理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特质: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式特质与价值特质。在形式上,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独立性与自治性匮乏、诸法合体、司法与行政合一等特征;在实体价值方面,它具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以及和谐主义的特征。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化特征。从公法与私法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典型的公法文化,尤其是刑法典形式特别彰显。公法化特征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中国古代官制法”,其渊源与结构足以与古代刑法争雄媲美。相比于公法特征的强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私法就显得很不发达了,“甚至在古代法律体系中无足轻重”(见该书第30页)。况且很多的民事关系要借助于刑法手段来调整,使古代民法淹没在庞大的公法中,“古代民法基本上刑法化了”。3.从文化特征而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全面地渗透着儒家文化的一系列原则和精神实质,例如在刑法中包含着的“亲亲”“尊尊”的等级制、宗法原则等,这些以“礼”为核心的儒家精神与原则对古代法律的渗透和主导使得中华法系具有极为强烈的伦理与教化功能。4.与西方法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更显现出其固有之特质。这种特质的凸显是在近现代中西法律文化之冲突中完成的。从法文化的整体到具体的亲属法文化,这些冲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示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和方向。
其次,在思考如何厘定西方法律文化时,作者抱有着极为清醒的头脑,即“正确认识近代资本主义法律文化中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应是学者们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见该书第85页)。关于如何对待西方法律文化,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即不加思索地认为西方法律文化的特质即是现代性法律文化特质,把现代性法律文化特质的优越性统统给予了西方法律文化,似乎法治、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等理念一直是西方传统的专利;甚至认为西方法律文化没有传统的累滞,它就是现代性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是指非西方地区的法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西方没有现代化的问题(至少在法制上如此)。夏锦文先生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法律文化发展三个阶段的观点来看,西方法律文化也有传统的问题,也有不适应商品生产要求的问题,也有消极性的方面。因之,作者认为“现代法律文化并不是只存在于某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法律文化中,而是存在于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不同传统的法律文化之中”(见该书第92页),不存在“不体现任何民族地域传统的那种纯粹的现代法律文化特征的汇合体”,“人类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子,既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是东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积极因素的共同之花”(见该书第93页),并且,人类社会的这朵“共同之花”正在汇合形成之中。
二
何谓法制现代化?它有无一个统一的标准?该问题的参照系是什么?我想这是任何从事法制现代化理论的学者都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必须解答的问题。在该研究领域,理论界有两种至少在方法论上成问题的做法:一是纯规范的研究,以一种极为精致的理论装饰把法制现代化构建为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二是为了追求知识的精确性、实证性,试图用多种数据等精确手段进行研究,有的甚至建立了一系列数学模式。应该说这两种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法制现代化研究说到底是一种应然与实然相结合的研究(关于方法论问题,我在下文还将具体论述),纯规范化研究或纯实证的研究都将使法制现代化这一话题失之于偏颇,流于虚妄和琐碎。夏锦文先生在《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一书中对此的处理是极富说服力的:既有“静态的理论模式设定,又以动态的方式描述法制现代化的变化图景;既有理论模型的逻辑演绎,又有细致入微的实证考察;既有历史主义的检讨,又有应然状态的探索。这是一种整体主义研究的典范,在国内同类著述中实不多见。下面按照其逻辑结构来考察夏先生的思考路径。
首先,作者以“法律效益化”构建了一个静态的参照系和“综合评价”体系,它由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构成,后两者又由各自的蕴含构筑而成。形式合理性蕴含着“法律的严谨性和完整和谐性”、“法律规范的实现程度”、“司法的程序合理性”、“法律组织的独立和专业化”;价值合理性蕴含着“自由”、“平等”、“正义”等法律价值意义上的基本准则或法律的价值取向。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在法律效益化这个统一体中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法律的高效益是形式目标与价值目标的统一体,是人类法律追求共同目标。
其次,如果说法律效益化的概念和标准是在静态的意义上揭示了法制现代化的性质、特征和目标,借以为一国法制现代化的水准、程度、方向提供评断的标尺,那么,要动态地分析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转变过程中的变化及特点,深入探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路径及其规律性,就势必需要进一步研究法制现代化的模式问题。
法制现代化模式作为夏先生从事动态分析的工具,并非是其为理论演化的需要而随意捏造出来的,而是有其方法论基础和社会历史基础的。以法制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作为划分法制现代化模式的依据或标准,作者将法制现代化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内发型法制现代化;二是外发型法制现代化;三是混合型法制现代化。在以此为参照系考察了法制现代化的不同模式之后,夏锦文先生特别强调了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和处理东西方关系。对此他抱有的非“唯西方主义”倾向是笔者最为欣赏与赞许的。他认为,在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早发的西方法制现代化模式对东方社会乃至非西方社会法制现代化进程发起了冲击和扩张,这种冲击虽然有助于东西方法律文化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同时也导致了非西方国家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扭曲甚至灾难,造成了法律发展的“泛西方化”。因此夏先生认为法制现代化的后来者决不能通过刻意模仿而实现法制现代化,它必须以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原则结合本民族的特点进行新的创造,从而以自己独具特色的法律文明发展样式汇人世界法制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伟大进程。因之,对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历史进程也应当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进行认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不仅体现了法律文化的民族性和本土化色彩,而且也反映了法律文明发展的世界性和国际化潮流,是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文化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结晶,是新时代条件下对世界法制现代化和法律全球化的伟大贡献。”(见该书第196页)
第三,诉讼法制是一国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制现代化形式化标准的核心所在。夏先生以此作为典型个案来分析近现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运作机理,其分析考察的路径是与对法制现代化的分析考察一脉相承的——从理论模型的构建到中西诉讼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传统诉讼法文化的嬗变,用历史主义和比较分析的手法描述了近现代中国诉讼法制的宏观图景,最后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分析了中国诉讼法制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夏先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树立了法制现代化研究、尤其是个案研究的典范。这种分析思路在本书的第四部分也有所体现。
三
一本著作的成功与否,除了取决于其所提出问题的质量及其回答外,另外还要看其进行研究、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这一研究领域中,固执地运用一种研究方法将会使研究走入狭隘和空洞。因为法制现代化本身即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事实,其所关联的因素不仅仅指向实证法条,更多地指向法条背后的制度、原则、观念,更宽泛一点它甚至包容着社会形态的所有方面。因此在方法论上该领域必须解决如下问题:研究领域既不能过窄,只就法论法;也不能过泛,将法制现代化置换为社会现代化。另一个问题是与该领域自身密切相关的,即在该领域必须要处置的传统问题和西方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该领域研究的关键。夏锦文先生在《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一书中给出的方法论答案也是启人深思的,其最大的特征乃是整体主义的叙事方式,将社会变迁与法律的发展紧紧勾连在一起,紧紧抓住社会现实的运动来反映法律的变化发展。夏锦文先生在该书中的方法论处理上有以下特点:
第一,历史主义的全线贯彻使整部作品对法的叙述更具凝重感、厚实感。众所周知,对现代法文化的把握我们往往囿于现当代的西方范畴,至多对西方法文化的发达史作一翻旁敲侧击式的叙述,很少将东方法文化的历史作为法文化的独特类型收入法制现代化研究的视野之中,很少将我们的传统作为现代化的发韧因素之一,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感的消失。因之,不能将传统纳入到法制现代化的宏观叙事中是当代法学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缺陷。在此层面上,夏锦文先生作出了很好的探索和尝试。他非但恰当地把握住了我国传统法文化的特质,而且以此为根基和发韧点,展示了中国近现代法制现代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宏观图景,这不能不说得益于夏先生恰切的历史主义方法论选择。
第二,比较研究方法的全面渗透使夏先生的作品更具可读性、立体感。作者对各类法文化特质尤其是对中西法文化特质的把握具有精确性,使读者能够恰当地领悟到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定位以及中西法文化冲突的实质与根源,也更能体味到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盲点和问题。当然,这种比较方法的运用不仅仅囿于中西法文化相互观照的范围,它还关联到传统与现代的考察。这种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使我们能够确切地感受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中西、古今的对峙脉搏,俯瞰法制现代化进程的真实面貌和深厚底蕴。
第三,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真谛在于把法置于现实的社会土壤中进行考察,以法与现实社会的互动关系作为描述对象来探究法的“真相”,夏锦文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广泛采纳了这类方法,尤其以第四部分为甚。以这种方式进行叙述,使法制现代化进程在我们眼前变得更为丰满、立体,使读者在法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中找到了法制现代化的现实轨迹和动力基础。
作为社会存在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作为对其进行理论概括与再现的法制现代化理论研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真实地在理论上再现和恰切地把握法制现代化的事实和规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方法论的科学与否,并且仅倚重一种方方法论资源,以辛勤耕耘的汗水、平和谦逊的心态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法制现代化这朵理论之花才会开得更为鲜艳灿烂。我想这也许是夏锦文先生通过《社会变迁与法律发展》一书给予我的最大启迪。
编者注:本文摘自《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4期。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