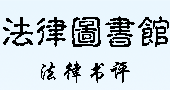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法律现代主义》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苏亦工 2006-9-6 13:50:17
与德沃金、昂格尔和波斯纳这些现如今在中国大陆声名鼎沸的当代美国法学家相比,戴维·鲁本这个名字听起来或许会让中国法学界的读者们极感陌生;同样的,《法律现代主义》[1]一书也绝不像《认真对待权利》、《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及《法律的经济分析》诸书那样在中国法学圈中广为流布。然以笔者拙见,本书之磅礴厚重、犀利深邃实在是别开生面,甚至更为切近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弊;更有助于我们反省百余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投身其中,苦苦探寻和追索却又无从自拔的所谓“现代化陷阱”。当然,如此比况,可能极不合宜,也难逃老王卖瓜之讥。顾名思义,本书讨论的主题是法律现代主义。那么,什么是现代主义、什么又是法律现代主义呢?依本书作者之见,“现代主义是对我们与我们自身文化之过去的复杂关系的一种反应。”[2]的确,说起“现代”,自然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无“过去”即无所谓“现代”;无“现代”也就无所谓“后现代”或“将来”。我们身居现代,当然难免会回首过去抑或展望未来。无论是回首还是展望,无非都是在思考我们现在与先前和以后的关联,因而作者期望:设法把我们与过去的联系这一问题变成“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主题。”[3]
有读者或许会提出,为什么不把我们与将来的联系作为我们现在正在从事的主题呢?这确是一个问题,作者似乎并未直接遭遇或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本书中所说的一段话或可作为对此疑问的解答:“我并不反对我们应当把目标定在实现总体上最佳结局的想法,我所反对的是以为最佳结局只能通过专注于未来才能求得的说法。……我不大相信我们的预见力,不过更为根本的是,我认为我们所寻求的结局很大程度上还得从往昔中获得。”[4]如此说来,作者期望赋予现代主义的使命是对历史进行审慎地思考。不是简单地依从或抛弃往昔,而是以一种非实用主义的、哲学追问的精神,透过历史来思考我们走向未来的道路。
《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作者虽为西人,未必听说过《大学》,但看来同样深谙本末先后之道。现代主义思潮最初是从艺术领域而非法律领域兴起的。故作者之思虑首先亦不是从法律现代主义而是从艺术现代主义开始的。作者认为,艺术现代主义是在彻底丧失了对传统的支配能力的自信心的情形下出现的。早期现代主义者们发现他们总是面对着康德的那个问题,即“凭借何种权利?”艺术也带有这种最终的严肃性,他们相信,任何一种艺术传统都要求存在的合理性。缺乏合理性,那种传统要想维持下去就只能靠欺骗,如果观众还喜欢它,那就是道德沦丧了。艺术现代主义者们相信,作为一个道德问题,传统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依据,甚或只能在其专属权威以外去运作。
由艺术现代主义,作者看到了现代性的普遍性。他指出:“现代性之生长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走到其发展线索的尽头。虽然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多重方式,但如果聚焦于从传统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这个单一的方面会更便于达到我的目的。”[5]
在作者看来,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法律领域:“法律目前正在面临着一种与艺术上相似的现代主义困境的现象”,[6]“旧有的形式不再令人信服,新的形式则更多的是批判而非积极的建树”。[7]简言之,艺术上的和法律上的现代主义均是对某种 文化上的危机做出的反应,是对已丧失了其合法性的制度和传统的一种感知。
据作者自道,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两个重大事件——即民权运动和越南战争——引发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危机,并因而触及到植根于自由主义的法律思想。本书各部分的写作,正是对这些事件做出的反应。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再深远一点、再开阔一点,这场危机其实并不局限于美国,也非始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那个世纪的前半叶,在欧洲发生的、殃及全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早已深刻地暴露了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恐怕在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丧失了对西方式法律制度之公正性的信心,甚至丧失了对西方文明鉴别公正之能力的信心。
无足骇怪,一向以自由、平等、博爱相标榜,一向以《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傲居各文明之上的西方,居然能在人类进入号称高度文明化的20世纪里明目张胆地集体屠杀 600万手无寸铁的族群,而且事毕仍能恬不知耻地捍卫种族隔离制度。真是斯文丧尽,法治荡然!这样的文明、这样的文化,难道还有多少人道和公正可言吗?难道还不该做出深刻地反省吗?那么,面对如此深重的文化危机,西方人做出的反应是怎样的呢?按照作者的归纳,大体不外乎四种选择。而这四种选择,艺术上的与法律理论上的大致可以互相对应。详言之,有实用主义的、有传统主义的,也有先锋主义的,或称虚无主义。这三种主义大体上说都是规避而不是正视这场危机。于是乎,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西方文化整体上陷入了作者所形容的“现代主义的困境”。他指出:“一旦感受到我们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的束缚,但又无从逃离和躲避,我们就很可能体验到我们的现代主义的那种无家可归般的困窘”,原因是我们既“无法保持在前现代主义的事业之中,但是又无法从根本上找到一种替代传统的资源”。[8]
不用问,那剩下的第四种,当然就是本书探讨的主题——现代主义。作者明言:“批判法学就是法律现代主义”,[9]因为“在当代法律理论脉络中,惟有批判法学派一家意识到现代主义者的困窘并……通过回忆而展开批判。”[10]
与艺术现代主义一样,批判法学也是对前述文化危机做出的一种反应。比较而言,作者显然对批判法学派及新左派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甚至在许多方面与其保持着一致。所不同者,作者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法治自由论者,一如既往地捍卫法治和权利,反对有关法律不确定性的论点、反对批判法学派对权利的批评。
中国古人论诗,讲究“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 彻”。本书开篇,以“吾辈哥白尼主义者”命名其导言,确有爆竹开花,振聋发聩之效。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正是哥白尼革命“把我们从一个封闭的世界带到一个不确定的宇宙”。[11]“导致了对我们在万物秩序中自身地位的重新评估,将我们从一种封闭的、地球人类中心的世界转入到一种不确定的、无关紧要的宇宙——进而,在这个宇宙上,我们并非惟一重要的,而只是混迹于其他众多自然现象中的一种自然现象而已”。[12]
1890年,薛福成途经香港、新加坡时,看到两地不过五六十年间即由荒岛变为巨埠,曾慨叹说“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13]仰慕西方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就在薛福成发出那番感叹不到半个世纪之前,在国人眼里,中国乃是世界之中心,天下之共主,“抚有万邦”,“威德覃敷,远无弗届。”蕞尔英伦、区区岛夷,何足道哉!谁曾想到,斗转星移,日月轮回,就是这区区岛夷的数叶小舟,几发乱炮,一夜之间,便搅得个老大帝国沦为了“东亚病夫”。
由此看来,鸦片战争对于东方世界的震撼恰似哥白尼的日心说对基督教世界的震撼。西方人在失去了上帝的庇护以后,开始重新寻找人的位置;中国人在失去了天朝上国、世界中心的想像以后,也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只是前者是自发的、主动的;后者是触发的、被动的。如果套用本书作者的观点,我们中国人其实早在19世纪中叶以后,即已体验到、而且至今仍在忍受着现代主义那种无家可归般的困窘:我们既丧失了传统的领地,又未找到新的家园;我们早已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束缚,却又无从逃避。
于是乎,先进的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了。最先看到的西人长技不过是“坚船利炮”,以为只要我们“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可反败为胜。因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掀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技术制造坚船利炮,以期御敌于国门之外。然而随着1894年甲午战争的败绩,中国人的洋务梦也告破灭了。接下来,先进的中国人又看到了西人的“良法美政”。1898年的戊戌变法及1902-1911年长达10年的晚清“新政”,堪称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二波。
但是势态并未因之好转反而有逐趋恶化的迹象。欧战烟火方熄,列强压迫又至。日本提出要接收德国人在山东的利益,逼迫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就引发了对中国近代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时候的“先进中国人”看到的已不止是器物和制度,还有西方的“新道德”和“新文化”。一方面,是要把泰西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来,全盘西化;另一方面是要“砸烂孔家店”,盖即对自己的旧文化的彻底绝望。林语堂曾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否拯救旧文化,而是旧文化能否拯救我们”,“事实上,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14]
一句“只有现代化才能救中国”喊出了多少代先进中国人的共同心声。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可谓不耻下问、不辞艰险。单以法律而论,我们是先学欧、继学日、再学俄、又学美,该学的都学了,该弃的都弃了。中国固有法律体系早已“亡国”了,中国现行的法律尽管带着种种暧昧、变异的色彩,但毕竟从整体框架上看已经完全西化了,何以现代化法治国的彼岸在吾人看来却愈见模糊、愈发遥远,简直就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呢?是我们学得不够认真、不够虔诚吗?还是我们的西方师傅们没有把那真经传授给我们呢?真是令人大惑不解。狄百瑞说过:“中国人认为‘道’是一种生长的过程,也是一种向外扩张的力量。同时根据孟子的看法,如果‘道’无法从他们本性中发现的话,那么‘道’不可能是一种真实与纯真的正理。不是内发的‘道’,将是一种外来的,同时有异于它们最基本的本性。在中国人近代的经验中很不幸的失去了 他们的自尊,放弃将新的经验与固有的传统消化 溶解。将所有的价值都看作是从西方来的,或将所 有的价值都以将来为目标,而不扎根于他们的过 去,这种态度使近年来的中国人无法从他们的本 性中找到‘道’的真理,这种脱离自己根源的结果与它强烈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中尤为明显。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真理的成长并不因此而停止,只是暂时被遮蔽。中国人民的新的经验将从内心中成长起来,而不再是一个单纯从外边输入的革命。”[15]
至哉斯言,亦可谓知本矣。我们要追求现代化、要塑造我们的未来,固然需要了解我们以外的世界,但首先还须了解我们自己,特别是了解我们自己的过去。那么我们凭靠什么去理解我们的过去、又应该如何去理解我们的过去呢?
贯穿于本书中的另一条主线是重构已经断裂了的叙事。通过重构叙事,将历史上的牺牲者们被遗忘的声音编织在一起,从而使我们真正领悟公正在现代社会中的性质。
的确,中国的历史悠久漫长,其间最缺乏的就是公正。小人得志,良善遭殃,黑白颠倒,蔽美称恶,差不多已经成了必然规律。五千年来,那被湮没了的、牺牲者们的声音正不知凡几,是否也应该重加编织呢?或谓一部二十五史,不知从何说起。可这最近百余年的历史,也未免声音太过单调了些吧,该否重新梳理一番呢?在西方,汉娜·阿伦特曾指出:极权主义致力于撒谎、恐怖及屠戮大众的事业;本雅明也说过:重视胜者、统治者的“文化财富”实在只是胜者的战利品,无恐怖,则无可思议”其所由来。[16]同样的,在东方,千余年前的宋儒也说过:“三代以道治 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17]三百多年前的黄宗羲更指出“后之为人君者……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 业……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18]
真是不谋而合!如此说来,古今中外的所谓正统的历史叙事大都不过是胜利者们的家谱。牺牲者们的声音总归是听不到的,即或听到,也是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纵然那胜利者中有个智愚贤不肖之别,仍不过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以至于道之不明、不行,“民散久矣”。本书下编的第五、六、七三章或许能为我们重新编织起那断续不清的声音提供一些理论佐助。
重构叙事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们长期奉为神明的科学分析方法自身的缺陷。作者指出,现代性的一个中心成就在于以科学理论作为我们的基准模式来理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并用以取代诸如史诗、圣经等经典叙事。然而,那种在自然科学中奏效的解释模式根本不可能告诉我们我们想要知道的关于人类的事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主义的困窘。
早在鲁本写作本书的数十年以前,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也提出过类似的见解:“迄今为止,我们是用现代自然科学里的古典学派的方法来探索文明起源的积极因素。我们一直是运用抽象的概念去思想,而且使用无生物来进行试验——种族和环境。现在这种办法既然是毫无结果,我们就该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失败是否是由于方法上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当同样地警惕,不要在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的历史思想时,采用专门研究无生物的自然界的科学方法。在我们最后一次努力解开这个哑谜的时候,且让我们另走一条道路,遵循柏拉图的方向。且让我们暂时闭起眼睛不看科学的公式,以便能让我们听得见神话的言语。”[19]
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提出要把西方的“赛先生”请进来,众多的自视为是社会先锋的中国人还试图引进某种先进的理论来科学地探索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进而指导我们的社会实践以实现所谓的社会进步。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我们实现了那样的目标吗?我们能够实现那样的目标吗?我们应该实现那样的目标吗?
或许正如本书作者所言:“在实际历史上最近乎成功地科学支配的东西就是极权主义。”“事实自身表明,政治科学中谈论的‘预测及支配’不过是黑色喜剧,化为愚蠢和恐怖。”[20]幸好昔日的秦始皇们试图发现长生不老药而未果,那万世一系的江山终于未能永固下去,这不独是炎黄子孙之大幸,应该也是全人类之大幸。现代的秦始皇们则试图通过发现、掌握并运用所谓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法则(或许还有科学的武器)来支配全人类的历史进程乃至主宰人类的命运。一旦成功,绝不要指 望陈胜、吴广辈的揭竿而起能阻挡住那“历史的车 轮”前进,整个人类只有集体接受作奴才的命运。
看来,现在似乎也是“该停下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
本书原著的封面是保罗·克利的画作《新天使》。依本雅明的想像,那画中的天使是“历史的天使。这个天使总是往后看,乃至无法停止对构成过去的那一系列不间断的大灾难的沉思。他想去修补那劫难后的残垣断壁,但来自天国的劲风吹开了他的翅膀,把他从后向前吹入了未来。本雅明痛苦地发现,这场大风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用本雅明的格言来说,正是那不可逃避的进步,我们天性中的全部劫数,将那脆弱的人类大厦吹得七零八落;正是那进步阻挠了我们的天使合拢起双翅,保持在其位置上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向我们伸出援手。所有他现在所能做的就只是沉思过去——当过去坠落时记住它,不至于让我们的成就消散得无影无踪、杳无形迹”。[21]
显然,本雅明的想像是彻底地绝望。不过本书的作者还是给我们点燃了一点希望:“也许我们的渺小容许我们奋发向上,避开那进步的狂风,从那历史的废墟中抢救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22]
本书作者戴维·鲁本出生于1949年,现任乔治城大学弗雷德里克·哈斯(Frederick Haas)法学和哲学讲座教授,是战后出生的第二代美国犹太人,其祖先来自波兰和拉脱维亚。我们从本书的字里行间中应能体会到犹太思想、宗教和文化传统,特别是犹太人多灾多难的历史对作者的思想、情感乃至学术取向所产生的显著影响,或许也正是这特殊的群体遭遇和文化传承养成了作者对被压迫、被奴役者的同情心,对暴虐、残忍的疾恶如仇,对平等、公正的执著追求以及对世界主义的真切向往。至少,这是笔者从本书中读到的作者。
《周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哲学家著书立言,大抵都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西方文明能够雄踞五大洲数百年之久,至今不衰,首先正是因为不乏像本书作者这样的忧患之士。但更重要的是,像本书这样的仁言良知,在西方世界,虽几经跌宕坎坷,终能由涓滴之水汇为江海之滔;由星星之火,化作燎原之势,奏出时代的强音,形成整个社会的普遍共识。
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足见中国社会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同样不乏忧患之士,同样不乏仁言良知,所欠缺的是全社会普遍的自我反省意识和过而能改的笃行精神,以致历史不断循环,谬种代代流传。
本书作者指出:“我们各种各样的斗争是为了细述过去的特权,这使得过去所蒙受的苦难获得了意义。”[23]中华民族号称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但我们最欠缺的恰恰是拯救过去的能力。因此除了重复以往的苦痛以外,始终未能赋予那些苦难以多大的意义。
“政治行动……其最初的也是最终的目标在于挽救过去。这种挽救不是象征意味上的;相反,如金氏那样,他认为政治行动改变了历史的结构,打断了历法上的次序并将过去和现在缝合在一起;通过重塑往昔——差不多是变成往昔,从而使现在挽救过去。……我们重新复活并拯救被奴役的祖先就要重新投入他们为自由而进行的战斗……”[24]
如果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都能从这段话的深意获得某种启迪,未来是否可以减少甚至避免那历史上频频重复的苦难呢?读过本书,如果说我有什么感悟的话,或许可用马丁·路德·金的那段名言和《国际歌》中的一段歌词概括之。金说:“立法和法庭命令只能宣示权利,永远也做不到全面地输送权利。只有当民众自己起来行动时,那纸面上的权利才能被赋予有血有肉的生命。”[25]《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笔者坚信:中国的前途必有赖于中国社会全体自身的觉醒,必有赖于所有的中国人同时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普遍的良知发现和道德自觉,舍此别无捷径。《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斯之谓耶?!
本书是一部法哲学著作,理论性极强,上编各章读来难免会感到枯涩乏味。建议有心阅读此书的读者不妨先从本书下编读起,读后如以为尚有余味可品,回过头来再读导言及上编亦无不可。
古语道:“《春秋》责备贤者。”我之特别推重本书,尤其是其第五章,也是想给我们的贤者们奉上一杯浓咖啡,催醒其久已麻木不仁的神经。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九州之大、四海之广、五千年文化积淀之厚、十三万万人口云集之众,不会没有这样义无反顾的勇士了吧?!
【注释】
[1]David Luban, Legal Modernis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以下皆称原著)
[2] 原著第380页。
[3] 原著第380页。
[4] 原著第279页。
[5] 原著第17页。
[6] 原著第380页。
[7]见中文版序(本书中译本即将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8] 原著第11页。
[9] 原著第51页。
[10] 原著第40页。
[11] 原著第18页。
[12] 原著第28页。
[13]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83页。薛福成(1838-1894),晚清著名外交家和思想家,自1890年起历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和驻外使节。
[14] 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320页。
[15] 《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1989年第二次印刷本,第128-129页。
[16] 原著第40页。
[17] 参见朱熹《近思录》并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
[18] 《明夷待访录•原君》,古籍出版社1955年版。
[19]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20] 原著第187页。
[21] 原著第391页。
[22] 原著第391页。
[23] 原著第278页。
[24] 原著第277页。
[25] 原著第244页。
编者注:本文摘自《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