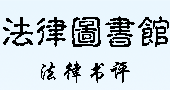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进步还是退步?》书评(1) —— 查看此书介绍
陈 韬 2006-8-29 16:44:07
几百年来,国际私法这个应该可以称得上古老的法律部门在各种精妙的,甚至是奇幻的学说和理论的交替支配下向前演进着,直至19世纪在欧洲大陆诞生了被学者们与哥白尼革命相类比的“法律关系本座说”,从逻辑上将国际私法推向了巅峰,国际私法前所未有地被改造为一台精密的法律适用机械,而且通过斯托里的“既得权说”在事实上取代了先前英美法世界模糊不清的国际私法规则。这一幅美好的图景似乎昭示着国际私法将在20世纪得到稳定的适用而只需进行现有机制内的小规模修补,这也是20世纪初散发着理想主义芬香的国际私法学者们由衷的期许。然而,英美法的实践理性传统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以冲突法革命的方式向传统的逻辑体系提出了挑战,从而再次将国际私法带入论争与迷茫,直到20世纪末,人们依然在困惑着,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针对这一也许注定无法廓清的迷题,国际比较法学会于1998年7月26日至8月2日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召开了第15次大会,中心议题即为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会议主持人、美国Willamette大学法学院教授西蒙尼德斯在18份国别报告的基础上提出总报告[1],也就是笔者在这里所要斗胆进行评论的主要对象。针对西蒙尼德斯的总报告,国内的著名国际私法学者李双元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私法正在发生质的飞跃》的评论[2],笔者在这里也斗胆就李双元教授的这篇评论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总报告从限定范围入手,提出国际私法所要面对的五大基本主题,最后给予简短的总结,体系简洁清晰,本文在此就不在另辟新途,基本上遵循总报告的这一思路。
一
既然总报告的标题中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20世纪末的国际私法较之世纪初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那么本文的主线似乎就是为做出最终的判断设置一个评判的标准并依照这个标准来审视20世纪的国
际私法。然而,总报告却在一开始就回避了这个问题,指出总报告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回答标题中的问题,而是提供一个讨论国际私法基本问题和困境的框架。李双元教授肯定了总报告所持的中立态度,认为
在评价标准必然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不应将个人的看法作为普遍性的结论。总报告所持的态度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私法问题较之其他法律问题的复杂性。国际私法所要解决的并非是给法律关系的主体设置统一的权利义务,而是要在两个甚至多个自足并可能自认为完美的法律体系中选择出一个作为准据的规范,这也就意味着国内层面的价值冲撞与国际层面的价值冲撞在国际私法中重叠出现,国家
与国家、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三对矛盾竞相角力,各种价值取向之间激烈冲撞的程度是其他法律部门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作为评论人,很难在令人目眩的价值冲撞中找寻到公允的判断标准,总报告所
持的中立态度与其说是主观上的科学态度,不如说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举。在回避了判断标准之后,总报告对讨论的问题做了范围上的限定,即只涉及冲突法领域,因篇幅所限不延及管辖权和外国判
决承认问题。但是总报告在这里出现了一段不大不小的插曲,即英国报告人芬提曼教授对总报告人这样的安排表示异议,并提出两项理由。首先,他认为英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案件时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花
费在中间程序上,在法律适用问题浮出水面之前,绝大多数案件已告终结,且当事人常根据英国法提交诉讼,因此冲突法在国际私法中不应再作为重心来看待。[3]这项质疑的消解是顺畅的,总报告在肯定该项质疑的实践意义的同时挖掘出了英国现象的历史源流和特殊的制度背景,不能把英国实践作为否定法律选择的重要性的普遍依据。李双元教授对总报告的分析持肯定态度,并进而提出了将管辖权放在
第一位会加剧法律适用中的“本地化”倾向。笔者认为,总报告和李双元教授在这个问题上的阐释是适当的和准确的。其次,芬提曼教授提出了外国法适用的困难将动摇法律选择这一尖锐而又现实的问题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阐述非常精彩。他指出,由于缺乏完善的程序制度,所以要保证精确、完整和及时地查明外国法,以及成功地适用外国法是不可能的,因此选择适当的准据法来抵制单纯地适用法院地法
的整个思想观念从根本上被动摇了。[4]外国法适用的问题虽然在这里只是一段插曲,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长期被忽视但又直接事关国际私法根基的大问题。众所周知,国际私法规则援用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
对外国法的适用,但是各国的法律都纷繁浩杂,一国的法官对外国的法律予以正确的适用几乎是远在其能力所及之外的,特别是习惯了套用法律条文的大陆法国家的法官更是无法捉摸英美法中那数不清的
判例。“对于外国法,他并不比当地的大学一年级学生知道得更多,而且常常是更少。”[5]与此同时,当事人举证和专家证言都存在严重的倾向性问题。可见,对外国法的适用本来就是一项虚幻而不切实际的工作,而国际私法也就成为建筑在虚雾之上的空中楼阁,一切对冲突规范的研究难道就是为了这样一个虚幻的、背离国际私法初衷的结果吗?因此,外国法适用的问题远非总报告中的一段插曲,而应成为所有国际私法学者关注并着力加以解决的问题。李双元教授在评论中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而总报告则对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予以了肯定,并意识到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二
在解决了总报告讨论的范围之后,总报告进入到对国际私法五个基本主题的考察和讨论。涉及的第一个主题是“多边方法、单边方法和实体方法之间的对立与共存”。总报告在这一主题的考察中回顾了三种方法的历史发展和兴衰变迁,从古罗马用于解决法律冲突的个案实体方法开始,到法则区别说时代单边方法的出现,再到“法律关系本座说”出现后双边方法对国际私法舞台的统领,最后在到20世纪以来单边方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新法律选择方法、单边冲突规范和直接适用的法三种途径的复归以及实体方法通过分割方法和国际统一实体法的途径复活和勃兴。总报告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对目前三种方法并存的状况做出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这种“方法的多样性”可以避免“拒绝症”,多少是国际私法成熟的表现,三种方法都是需要的,如果相互之间适当地协调合作,就能比单一方法产生好得多的国际私法体系。总报告对三种方法的历史演进和现时状况所做的宏观梳理在相当程度上是明晰和精准的,对现状的评价也是切合实际的。笔者在整体上肯定总报告的同时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首先是关于单边方法的涵义问题。总报告在使用“单边方法”这个表述方式的时候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情况。总报告在开始部分界定单边方法和介绍单边方法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将单边方法等同于法则区别说,即根据相互冲突的实体法的具体内容,力图从它们隐含的法律目的中推断它们欲有的适用范围,据此认定适用哪国或哪州的法律。然而,总报告在纵跨五六百年后介绍单边方法在20世纪的回归时却莫名地将其改头换面,成为适用法院地法来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并以本地化倾向明显的政府利益分析说、在运用最密切联系时考虑法院地相关政策等为例。总报告在单边方法涵义上的这种前后矛盾之处着实令人感到不解,依照目前国内学者的通常看法和本主题下所要阐述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应将单边方法界定为“适用法院地法来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为宜。李双元教授在评论中也敏锐地发现了总报告在单边方法的涵义上所存在的问题,并参考了胡永庆博士的论文考证了法则区别说实际上也是一种双边主义或多边主义的方法。李双元教授在这一问题上所做的纠正和补充是必要和适当的,恢复了本主题下体系的严密。当然,单边主义方法就不能再以法则区别说为例,而应前推至封建主义的属地法时期了。
其次是关于“个案实体法”的问题。总报告将罗马的万民法视为解决法律冲突的个案实体法方法,认为罗马外事法官注重特定案件的实际需要,从所涉各国的法律中总结出最合适的实体解决方法,而不是只选择一个国家的法律,还不顾这种选择在特定案件中可能产生的结果。对于总报告的这一观点,李双元教授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他认为罗马法官采用实体法的方法是由于鄙视其他国家“粗陋”的法律而非进行协调,此外万民法应为罗马国内的成文法而非跨国实体法或统一实体法性质的法律。李双元教授的观点在沃尔夫教授的著作中得到了支持,沃尔夫教授认为:“罗马的法学家……对于本国法律的赞赏是合理的,但是由于他们赞赏本国的法律,可能使他们中间很多人轻视所有外国法律,包括希腊法律在内,以至他们连想也没有想到须要建立一些规则来适用这样低劣的法律。”[6]然而,彭梵得教授对万民法的介绍却与上述观点相逆,根据他的介绍,当时在围绕地中海盆地的文明民族之间,共同的起源、古老的和频繁的交往、共同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早已造成大量的共同习惯和制度,再加上罗马人在自己的公民同这些外国人的关系中,并不象在现代国际法诉讼中那样根据情况适用自己的法律,而是适用这些共同的规范,当没有这种规范时则尽可能从各种不同的规范和制度中提取比较简单的内容,去掉各民族特有的成分,因而万民法确实可以被定义为罗马人与古代文明民族共有的或在同他们的关系中逐渐创立的规范总合。[7]彭梵得教授的阐述在格罗索教授的《罗马法史》中得到了证实,此外《罗马法史》中还介绍了罗马外事裁判官的善意审判在万民法形成中的作用。[8]由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总报告的观点是符合史实的,而李双元教授的质疑则与事实相歧。总报告在论及20世纪的国际私法时认为分割方法是一种个案实体法方法的回归,李双元教授对此也表示了认同。笔者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所谓的实体法方法应是在融合各国法律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自成体系的法律规范,具有内部的同一性,然而分割方法不过是对同一法律关系的不同法律问题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从而导致不同国家的法律分别针对不同的法律问题而适用于同一个法律关系,这一方法只是依据冲突规范将不同国家的法律简单地拼合到一个法律关系中,不存在各国法律的融合,甚至这些法律之间还会发生冲撞,连同一性也难以保证。可见,这样的分割方法与个案实体法是相去甚远的。同时,李双元教授提到的友好仲裁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友好仲裁允许仲裁员在当事人的授权下适用“跨国法”或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断人的名义处理案件,而这种公平与公正的观念很可能就是综合考虑有关各国的实体法所形成的。这种友好仲裁的方式倒不妨可以视为个案实体法方法的一种回归。
第三是关于近代以来三种方法的演进背后的历史根源问题,这个问题总报告和李双元教授的评论都未涉及,但笔者认为这一深层的问题还是有必要在这里予以简要地补充。实际上,近代以来三种方法的
演进都是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相照应的。自14、15世纪开始,特别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至20世纪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要求国际协调的呼声与日俱增,最终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巅峰
的19世纪诞生了国际私法史上最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并由此奠定了双边主义的时代,在国际上判决的一致和确定被提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之上。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向垄断阶
段过渡带来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大量干预以及对本国利益的更多关注,从而引发了单边主义的回潮和直接适用的法的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国际经济交往的纵深发展和各国单边主义的回潮也推动
了国际统一实体法的日渐成熟。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在此不做过多的展开。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