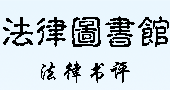鉴证:一位女记者眼中的脑死亡《中国脑死亡鉴证-关于死亡新标准的公众调查》书评 —— 查看此书介绍
舒盈 2005-3-20 21:45:29
鉴证:一位女记者眼中的脑死亡作者:舒盈 新闻来源:法制日报
人类绵延不绝,一代一代,有生有死。死亡,古老而现代的话题。脑死亡,死亡话题中最前沿的话题。陈雪春的《中国脑死亡鉴证———关于死亡新标准的公众调查》,说的就是这个前沿话题。
刘海若,引起中国乃至世界关注的凤凰卫视的节目主持人。一句比千钧还重的话“英国判死,中国救活”,引起关注的,既有对刘海若生命的关爱,还有对“脑死亡”的科学鉴定。刘海若是脑死亡吗?脑死亡还能活过来吗?脑死亡,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关切。从刘海若说起,到刘海若结束,这本书就是在这个极大关切的背景下,走进这个前沿阵地的。
谈这个话题的,不是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也不是满嘴学术词汇的医学专家,是一位报社女记者,她是苏州姑娘,她眼中笔下流出来的死亡,温柔而明亮,轻松而深邃,是学术而没有艰涩的学术味,是医学而没有一点福尔马林的气味。
脑死亡,早就接触的一个概念;可是,真正知道的,真正深入到这个概念里面去的,对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来说,并不多。就是天天与死亡打交道的千千万万白衣天使,也未必对这个学科,尤其社会学里的脑死亡知道得很多。这个脑死亡报告,是对脑死亡科学的全息调查,脑死亡学诞生、发展的历程,脑死亡在中国的历程,脑死亡的标准,脑死亡为什么要立法,真正实施脑死亡还要走多久,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中外医学专家的精辟见解都采摘于此,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本脑死亡学的百纳本。
脑死亡的鉴定并不难,要实施却不易。脑死亡不只是一个医学的专用名词,科学与伦理,情感与法律,交织在一起。脑死了,心脏在跳动,怎么就宣判这个人死亡了;心脏还跳动,怎么可以将肝、眼睛、肾脏移植给他人;人没死,要是医生作奸犯科或谋杀或盗卖器官,怎么办,这本书封面上有“公众调查”四个字,确实,公众、专家、医生的看法,广集于中。一条主线,脑死亡是人类个体终结的科学,脑是人类的中枢,脑死了,一切都死了,判定一个人是否死亡,脑死亡最科学。“一个人死了,他的物质的生命也就结束,脑死亡标准的推行,正是为了更准确、更科学地证实他的死亡。”脑死亡,同样讲伦理,同样讲道德,同样讲情感,那是科学的伦理,科学的道德,科学的情感。实施脑死亡,不可避免是一场争斗,是同旧道德、旧伦理的决裂,还是死亡领域里的法制建设。看了这本书,对死亡明白了、明亮了、轻松了,就是懂得了好好生好好死、优生优死的道理,不能不说这也是人生根子上的思想解放。
中国是伦理学的大国,积淀几千年,深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积于家庭每一个成员,植于生养,归于死亡。这本书别于医学著作,长于学术报告,独特之处,把触角伸进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理念,又与现代文化现代理念连接起来,深邃而不泥古。孔子的“未知生而焉知死”,庄子击瓦唱歌送妻死去所凭的“气”,海德格尔的“人是走向死亡的存在物”,都给伦理学注入了唯物论。这是一面。另一面,中国的伦理,东方伦理,给死亡注入了更多的“人情世态”,给实施脑死亡设置了重重障碍。死亡,需要人类的坦然,需要人类的理解。所以,这也是人人都应读的死亡坦然学和死亡理解学。拿书中的话来说,脑死亡“是一座人类深刻认识死亡的里程碑,是一本崭新的关于生命的宣言”。
脑死亡,是讲利益的科学。一个脑死亡靠外在力量维持生命的人,一天需要花掉数百上千的费用,几年下来数十万,而脑死亡人的器官,可以救治许许多多器官受损害的人,顽强论是医药资源、医疗资源,还是对亲属和社会的负担,都是一个很大的利益空间。推行脑死亡,既是人类的进步,也能合理使用有限资源。医学专家一再申明,推行脑死亡,不是为了移植器官,不是为了节约金钱,但确实存在利益和负担问题。大家都接受了脑死亡,全社会都认同了脑死亡,不存在道德和良心的责备,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大好事。通过这本书,而普及脑死亡学说,那就功莫大焉。
陈雪春,本书的作者,擅长写散文,擅长捕捉新闻的女记者,无论是新闻,无论是散文,无论是论说,哪怕几句话的“旁白”,都别有韵味,完全可以把篇死亡学说的长文,当作精美的散文来读。“这个开满鲜花的5月对于刘海若来说却是阴霾密布。假如没有那场车祸,这位凤凰卫视的金牌主持将和往常一样绽现灿烂笑容,有那么多喜爱她关注她支持她的观众。但事实是,那场车祸发生了……”
========================================= 本栏书评仅代表撰写者个人观点========================================